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内容简介
作为西方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柏拉图,其最著名的作品《理想国》的世界影响不言而喻。其主旨就是要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内容也是围绕着这个主旨展开论述的。在我国早已出现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作,但这些著作,虽然声明是从原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实际上大多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岳麓书社出版的顾寿观译柏拉图《理想国》,是一本真正意义上从原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并参考了多种英、法、德译本和注本,同时参考了最新的西文和中文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力求贴近原文语序、语气,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汉语的流畅,以致个别地方或过于支离,或过于冗赘,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原希腊文原有的味道,以满足有兴趣的读者深入研究。
下载说明
1、理想国是作者(古希腊)柏拉图创作的原创作品,下载链接均为网友上传的网盘链接!
2、相识电子书提供优质免费的txt、pdf等下载链接,所有电子书均为完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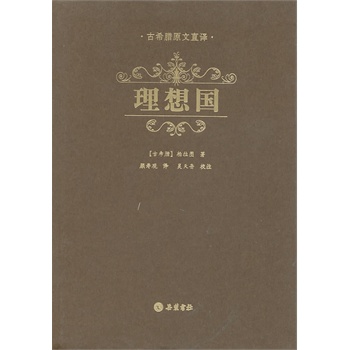
你且来听我的譬喻,也好让你更加知道,我是经过怎样的苦心才安排出这样的一个譬喻的。因为,这些正直的人们,他们在和城邦的关系上的处境是这样地艰难,以致再也找不出一个什么其他的、单个的、可以和它比尼的困境了。而必须把很多境况聚集和拼凑起来,从中安排出一个能够譬喻这种境遇并且能够为这些人进行辩解的事例和比拟,就像是画家们,他们要聚合和混杂很多东西,才能画出一只四不像的麋鹿或诸如此类的事物。你且设想一下这样的情况,不论这是关于一只船队还是关于一只单个的船只的。船主,不论在体魄和力量上都是超乎一船之中的一切众人之上的,但是耳聋、重听,目光短浅而对于航海事务的一无所知,则可以和以上两者的短缺相侔相埓。水手们,互相吵闹,争夺掌舵的权力,每一个人都认为应该由他掌舵,尽管从未学习过技术,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师傅,也不能说出他是在什么时间学习的;不止如此,他们声称,这是不可能教学的,而且,谁要说这是可以教学的,他们就预备把他剁成肉浆。这些人,他们整天徘徊,包围在那船主的周围,纠缠,要求他,无所不用其极,为的是好使他把船舵交付给他们;有时候他们没有能说服他,而是别人却说动了他,他们就把这些别人杀掉或是扔出船舷之外去;他们用麻醉药,用酒或是用什么其他东西把那尊敬的船主的手足捆绑起来之后,就自己来管理,指挥船只,把船里的仓载都拿出来享用,他们畅饮,豪宴,酣欢作乐,如此驾着船航行,就像在这些人来说,人们完全可以想见的那种情形。不止如此,凡是,无论用说法还是用强迫船主的方式,能够曲尽所能地帮助他们取得权力的人,他们赞美这些人,称誉这些人是航海家,是舵手,是航行事务的大师;而凡是不能这样做的人,他们就斥责他,说他是无用的人。而关于一个名实相符的真正的舵手,他们却殊不知晓,那是必须地对于年月、季节、天象、星座、风向以及一切举凡与他的技艺有关的事都有所钻研和通晓的,如果这个人真正地是想要成为一船之长的话,至于一个人如何去驾驶好一条船,不论别人是否愿意他去驾驶,这件事,他们认为,不论他的技艺和它的实践,都是不可能获得的,并且同时也就是说那航海的技艺[是不可能获得的]。船上的情形既是这样,那真正地是一位舵手的人,你认为,他事实上能不被人们,不被那些处于这种管理状况下的船只上的水手们称作是一个两眼朝着天上的星星的、闲嘴嚼舌的、一无用处的人么?
这段对话既是《理想国》里面船喻的相关段落,这也成为后世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比喻(同时在本身出现还有蜂群的比喻,两个比喻都被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当中讨论,著名的例子还比如洛克的《政府论》下篇讨论群众革命时也采用船喻),需要指出的是以航船来比喻统治,一方面是希腊特殊的地缘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希腊史诗里面已经有了关于城邦执政者比喻为船长、舵手的情况,当然柏拉图这里做的这个比喻也是有丰富的内容。 从整体上来看,这个船喻至少起到了两个大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是柏拉图指出了哲人统治城邦的正当性并不来源于众人的同意,而是来自于驾船技术(统治技艺)。另一方面巧妙地为其恩师苏格拉底(主要是指青年苏格拉底,跟随阿那克萨戈拉等学习自然哲学,柏拉图的《斐多》记载了他对苏格拉底的影响,也记载了苏格拉底的自觉转向)被阿里斯托芬嘲讽为只呆呆仰望星空的澄清。在柏拉图的辩护就是,苏格拉底的仰望是如船长一样在观察天象、星座、风向等,并非是无所事事甚至呆头呆脑,这些观察活动也并非无益于城邦治理,而是对航海(对应为城邦治理)至关重要的准备。 第二个方面的解释,还是要回到《申辩篇》里面苏格拉底面临的法律指控,同时包括道德意义上的很多人的不理解。对于一种不理解便是认为哲人是对城邦的“无用”。 在这两个方面的双方对照下,柏拉图表现了哲人在城邦中的应然位置和实际处境之间的差异原因,在船喻中哲人本来是最通晓航海技艺者(同时也是并不怎么通晓如何争夺舵手技艺者),但因敌不过权力和享乐欲望激增的群氓之迫使而失势,成为了一个在他人看来的无用之人(注意这里的哲人并没有护卫者,或许也在另一个角度证实护卫者阶层的必要,而且是对内统治保护哲人的必要而非对外防范外敌入侵的必要,同时柏拉图或许也向我们展示了“无护卫者的哲人”应该如何谨慎行事,不宜直接与城邦众人起冲突,懂得审慎)。 如果说无用性只是不理解无甚影响哲人的“消极自由”(借用20世纪思想史学者伯林的政治哲学概念),另外一条指控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则是严厉而破坏性的,这种指控将直接限制哲人到市场上寻找青年传授知识和交流学问。在船喻当中,柏拉图也仍然巧妙地给出了辩护,与《普罗泰戈拉篇》和《美诺篇》对美德不可教的观点相反,柏拉图这里尤其强调了航海的技艺是可教的,而众人却十足否认这一条。在柏拉图看来,愚笨的众人阻碍哲人自由地教导青年,其结果只能是让冒充的舵手掌舵,【城邦的弊端是不会有一个尽头的】473d,不仅败坏了哲人的荣耀,而且让城邦陷于不义者之手。 总体而言,船喻至少回应了城邦对哲人的两个异议: 1.哲人对城邦毫无用处,因此哲人的学问研究只是诡辩空想无甚价值,得不到众人的重视。 2.哲人的自由传授知识会败坏青年,因此要严格限制哲人的自由活动。没有一个人会自愿地去进行统治,没有一个人会肯自找麻烦,把别人的困难挑起来当做自己的担子,相反,他要求酬报;因为凡是有意于正确地施行他的技艺的人,既不去谋求他自身的最大福利,也决不去规定和厘定这样的福利——如果他真实按着他的技艺去做规定的话——而是相反,去谋求和规定那受他统治被他管理的人的最大福利
苏格拉底这一段用分析的方法做理解大概可以这样描述: 1.任何人(全称量词,因为原文用了“没有一个人”,亦指不存在例外)都不愿接受统治,这里的“统治”主要指的是政务或家务的烦劳部分,而不指涉福利。其实也就是说对所有人而言都没有动机自愿接受统治的劳役部分,用逻辑的逆否命题转换一下,倘若某一人接受了这种统治之劳役,那么必然是有某种外部的补偿,即酬劳。 2.正确施行技艺者却只谋求被他统治和管理的福利,而不计算和厘定自己的福利。 单纯抽离出来这个段落,苏格拉底的这个说辞是完全内在矛盾的,施行技艺者关注与被统治者的福利就是一种统治和管理工作,他居然又没有自己个人的福利考虑,跟第一条抽象的规则相悖。 对于这个逻辑矛盾,柏拉图刻画的苏格拉底紧接着给出了进一步说明,其实我倒是比较奇怪,善于辩论的特拉需马科为何不能够很快找出这个岔子,也可能是苏格拉底的发言连贯吧,上面的矛盾和他给出的解释在一个段落里面,没有给特拉需马科插嘴的机会。对于凡是有意进行统治的人来说,就必须备有报酬——这,或是金钱,或是荣耀;或是,如果不去进行统治的话,报之以惩罚
苏格拉底给出了施行统治的人还是要获得酬劳,并给出了他所能理解的三种(金钱、荣耀和避免惩罚)并且在他看来这三种构成了酬劳的全部,并以此作为论证的又一个立足点,而接下来苏格拉底对他理解的最优秀的人行统治又排除掉了三种的两种——金钱和荣耀,所以只有避免惩罚是那些人自愿行统治和管理的动机或出发点。你要知道,那些优秀的人既不是因为金钱的缘故而决定去进行统治的,也不是因为名誉的缘故。因为他们既不愿公开地,由于他的统治,去领取薪金,从而被人称为佣厮,也不愿意隐蔽地自己从他从自己的统治中攫取酬报,从而别人称为窃贼;又,也不是由于名誉的缘故,因为他们也不是贪图名誉的人。因此,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要他们去进行统治,没有强制和惩罚是不行的。
上面这个段落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也不愿意隐蔽地自己从他从自己的统治中攫取酬报”里面的“酬报”主要还是指的物质福利方面,跟上文说的“必须有报酬”的“报酬”的范畴不同,在这个语境当中“报酬”要比“酬报”更宽泛。 而这里特拉需马科跟我们普通读者一样,对苏格拉底给出的报酬包含给以惩罚抱有不解,我想说他的这个质疑也是有道理的,从语用的角度我们语言里面一般将福利增益的事情才视为报酬,而不会将避免潜在损失视作为报酬。当然,这里特拉需马科跟我们一样也只是对苏格拉底用词语用给以修正,其核心观点还尚未遭到攻击。 在这里,我想在更加要害的部分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这个《理想国》的核心提议给出质疑: 1.强迫哲人进行统治,若不行统治则给以惩罚。那究竟谁能够“强迫”哲人,又有谁能够“惩罚”他们? 2.强迫哲人统治的政治提议和政治安排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么? 3.哲人排除金钱和荣耀的论证缺少,那么是否存在有种可能,基本是为被统治者的福利而统治的哲人是否会“退化”,他们倘若蜕变邪恶又如何应对?我们将不能接受他进入一个期望有优良的礼法而治绩井然的城邦,因为,他唤醒并抚育这个灵魂里的薄劣的部分,使它壮大起来,并且扼杀那个理性的部分,这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所发生的一样,如果有人使坏人成为掌权者并且把城邦交付给他们,而把优秀的人消灭掉。正是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说,那以模拟为事的诗人也是把一种恶劣的政体塞进到一个个人的自身的灵魂里去,去取悦于灵魂那不智的部分,后者不辨多少大小,把统一的东西一时说成大的一时说成是小的,他以幻术制造种种映像,而与真实处于远远相距的位置上
“我懂了。”他说。“你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我们在讨论和叙述时所建立的城邦里,在那个存在于我们的理念中的城邦里,因为在地面上,我想,它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 “可是,”我说,“在天上,对于凡是愿意去观看并且在观看中愿意在自身之中建立一个城邦的人来说,也许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模型的。但无须乎去问究竟它在地上是存在的呢还是尚有待于存在,因为他只皈依于这样一个城邦,任何其他的都是与他无关的”
那就,看来,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我们也应该要对那些想要来有所讲述的人给予一定监督,要求他们不要像现在这样一味黑暗地刻画和谴责地狱里的事,而是毋宁要称颂和赞美,因为这些人讲述的既不是真实,并且也不利于激励和鼓舞那些预定是要在战争中扬威耀武的人
“这一方面的故事”主要值荷马史诗《奥德赛》里奥德修斯的地狱见闻和对地狱的描述,这个描述最好还是通过完整阅读《奥德赛》获得,包括奥德修斯为何要进入地府,见到了哪些特洛伊英雄又是如何具体的交谈,奥德修斯看到的地府是怎样的样子。 结合这段文字在全书第三卷的位置,其实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出来有关建立言论审查制度的教诲,因为在柏拉图看来,有些诗人对地府的恐怖描述并不真实也会让城邦的守卫者会因为害怕死亡而在战争中退缩。 有关这个言论审查制度,施派的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面曾经专门特殊描写,因为在当今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伦理世界,大部分的读者会惊异于柏拉图何以需要审查别人的言论,为何不是约翰·穆勒在《论自由》那样让真理通过自由市场的充分辩论而让真理得胜。不管怎么样,柏拉图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小穆勒,柏拉图的思路就是哲人-王直接的言论审查制度,摒退这些影响理想城邦塑造的诗歌,让这样的诗歌不予以流传。如果护卫者之中产生了一个质量较次的后嗣,就应该把他送到其他阶层中去,而如果相反,从其他阶层中产生了一个优秀的,就需要把他提升到护卫者中来。这就是为了要表明,同样,其他的城邦居民们,凡是与他的天性所契合的,就应该,按一个单一的人一项单一的工作的原则,分配他从事于每一件这样的工作,从而,每一个人照管一件单一的属于他本人的事。他就不会变成很多人,而是知识一个单一的人,并且同样,那整个的城邦也就成为一个单一的城邦,而不是很多的城邦了
还有,一人一事,各从其性 的建构性原则在本书多次被论及,比如183页433a部分重新谈到理想城邦与人的天性。我们所一开始就肯定下来,并且确定必须在一切之中都要加以贯彻的那个原则,它,或者,他的某一形式,我认为,就是我们所说的正义。要知道,我们是这样肯定和确立下来的,并且我们又不断地说到它,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就是:每一个单个的个人应该只照管有关城邦事务的单一的一件事,对于这一件事,这一个人的天性是最为适合的
但是,因为我同意如果这样的政体能够实现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存在的,并且此外还有无限的好处,因此就请你不要再只是讲它本身了,而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一点上努力试着来说服我们自己,这就是:这样的政体(或城邦)是可能的,以及它是如何可能的,其他一切我们都由它去吧
对于格劳康的这个提问,苏格拉底的回应如下文,苏格拉底在这里用来一个暗喻,构建理论和阐述理论犹如行军作战,而格劳康的提问有如敌军发动的突然袭击。对于这个理论如同行军的比方,实际上还是阅读列奥·施特劳斯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时所深切体悟到,而读了《理想国》才发现其实柏拉图老早就已经有了这个比喻,施特劳斯并非是远程,马基雅维利也不是,他们都是师法古之先贤。“你可是”,我说,“对我们的辩论,可以说,发动了异常突然袭击哩!而且,你对我现在这样的磨蹭和踌躇不前也没有表示什么同情。因为我想你也许不知道,在我勉强把两个浪潮避开过去以后,你现在就是把那三重浪潮中的最大和最汹涌的一个向我滚压而来了”
这里需要阐述的便是所谓的“三重浪潮”,这三个浪潮全部出现于本书的第五卷,三重浪潮其实是苏格拉底所面对的三次理论方面的质疑与攻击,实际上也分别对应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的三层的骇人观点(相对于古希腊的雅典)。这三个浪头的前后与逻辑安排必定有其深思熟虑,按照柏拉图的预想是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凶猛,最为难以招架的是第三波。格劳康这里的质疑实际上便是第三波浪潮。 首先说的是前两波,实际上格劳康的提问是根据前两波苏格拉底的阐述而来,也就是逻辑上第三波的冲击完全是前两波的逻辑顺延导致,因为格劳康提问的不是前两者的可欲性问题,他发动的这次“突袭”是追问苏格拉底前两者的可行性或实践可能性的问题。 第一波责难的观点是苏格拉底认为护卫者阶层男女享有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这实际上面临雅典的传统礼法对其的检查,苏格拉底要给出可欲性的证明。 第二波责难的观点是苏格拉底认为最佳城邦应该在护卫者这里女人和孩子归城邦所有,也就是进一步破除护卫者阶层的一切相关的私有根源,目的是为了实现“破国为家”,苏格拉底照样也是需要给出可欲性的证明。 而第三波的责难是针对前两者陈述的原则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实施,以便塑造最佳城邦。而苏格拉底给出的回答很简单即哲人为王,为此苏格拉底要搞定这个浪头,大概用了第五卷到第七卷三卷,甚至延续到后面的八九卷都可以说在回应哲人为王的这个伦理与实践问题。而这件事,看来,可以说,并不是什么,就像在儿童们掷贝壳的游戏中,贝壳在瞬间的一翻转而已,而是灵魂,从黑夜般的昏晦的日子里转过身子来进入真正的白天,这是一条向着“是”的上升之路,后者,我们将要说,它是真正的哲学
《理想国》这里表达的教育哲学或许被很多人诟病,这种“灵魂转向”的说法或许很神秘,很接近宗教,某种程度上跟禅宗的顿悟或许有一比吧。在洞穴隐喻的背景下,灵魂的转向更加有其情节与联想。之前阅读的艾伦·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是充分阐发了这样的教育理念,对于身边的绝大部分而言,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洞穴当中,从意见中开始也在意见当中结束,终其一生他们的灵魂昏暗未能见识到任何的光亮。而教育的起点也在此,教导人从洞穴中走出,爬升,走向那光明的地面。 最后,还务必强调的是柏拉图的灵魂转向还有一次,是哲人达到地面后灵魂会再次转向洞穴的众人,哲人并不长久地居于光亮之下,至于为何,可能是整本书的最大悬案了。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爱某一件东西,如果我们这话是说对了的话,必须能表明这个人是爱这个东西的全部,而不能是什么他爱它的这一个部分,而不爱它的那一个部分
这里还可以附带说一句,从这个段落的上下文看,苏格拉底比较清楚格劳康还是现代人说的同性恋,有男宠,不过看过《会饮》的同学应该也不会大惊小怪,古希腊的雅典有这样的男同搞基的风俗,其实苏格拉底也有嘛。 做一个个人的阐述,基于爱欲的对一个人的爱与基于爱欲的对智慧与真理的爱,二者是怎样的一个高低或位次关系,恐怕这是每个哲学青年必须要在实践中回答的问题,是对人之爱恋之上是否需要有逾越其之上的东西,比如说智慧与真理的爱呢,或许男女之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分歧。就像是从一个瞭望台上看下来一样,因为我们的讨论已经登上了这样的一个高度,我看到,如果说品德的形式只是有一种,那么恶德的形式却是有无量数地多种的,而就其值得注意的来说,就四种……拥有这些形式的政体的样式有多少种……看来,很有可能在灵魂上也如此……我说,同样,在灵魂上也有五种
第四卷后半部分已经达致一种高度,文中的苏格拉底暗示已经达到瞭望塔的最高处(一般到至高点才会停下来俯视下面)。按照苏格拉底的原意应该是达到至高点后往下“俯视”,进一步讨论各种政体的样式,但从本书的实际情况看五种政体直到第八、第九卷才充分开始,第四卷和第八卷直接被插入了第五、六、七三卷,苏格拉底在这三卷中迎来了格劳康、阿黛曼依特、波策玛尔科等人的三次提问浪潮,苏格拉底被滞留在最高处足足有三卷。 以上基本对第四卷及其以后的脉络发展有了一个梳理。 在上面的一段话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几个数字之间直接看并不协调。需要做一个协调,《理想国》里面事实上讨论的是五种政体,那么按照这里苏格拉底的说法就该对应有灵魂相关的五部分,但事实上苏格拉底说灵魂是三个部分,这之间是否有一些出入?还遗留了一个问题,这五种政体与城邦大灵魂对应关系如何,苏格拉底说的四种值得注意的恶德又是具体哪些?或者哲学家们在我们的这些城邦里是君主,或者那些现在我们称之为君主或掌权者的人认真地、充分地从事哲学思考,并且这两者,也就是说政治力量和哲学思考,能够相契和重合,而那许多形形色色的在这两者之中只是单纯地事其中之一的人们被严格地禁止这样做。不这样做,那么,亲爱的格劳康,我们这些城邦的弊端是不会有一个尽头的,并且,在我看来,人类的命运也是不会有所好转的。而且,我们现在在理论上所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政体,在此之前,也是不可能在事物所允许的可能限度之内发生,并径而能见诸天日的。但是,这个问题却正是那一直使我踌躇而不去讲它的问题,因为我看到,如果我把它说出来,它和一般人的看法会有多么大的距离;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不论就私人或是就公共生活来说,除此之外,别无任何其他幸福的蹊径可言
那么在看:那在言语中的欺妄,它在什么情形下,对于什么人来说,是有用的(东西)并从而是不该对它憎恶的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当它用来反对敌人们,或是用来阻止那些可能成为朋友们的人,当他们由于疯癫或是其他心智失常的原因要去做什么坏事的时候,为了驱邪避祸,它就像一种治疗的药物,成了有用的东西了?以及这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神话故事中,由于不知道古时候的真情实况是怎样的,我们就用欺妄来尽量地描绘和模拟真实,并从而使它成为有用的东西了?
如果把《理想国》的核心落脚点视作正义,单个人的正义和城邦的正义,那么在道德哲学上就很快来了一个问题,欺妄与谎言是否可以是正义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乃至理想的政治-生活秩序当中在很多场合不得不采用谎言。柏拉图自然也很清楚必须回答此问题,因此在《理想国》的若干地方都严肃对待,上面这一段是第三卷非常典型的。 在书的多处,柏拉图都以谎言比作药剂,这当然是在正义意义上的论证,在某些情况下一部分人说谎是正义的,而实言相告却成为不义。 在上面的一段话当中,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给出了可以使用欺妄与谎言的三种情形,对比联系后面的部分,实际上谎言的使用并不限于这三者,至少在选拔城邦统治者的时候柏拉图也同意可以采用欺骗来作为考验手段,这里先总结上文当中的三种情况: 1.用来反对敌人,大概特指的是城邦处于战争状态中不可对敌人诚实,要对敌人说谎 2.阻止朋友与潜在的朋友做坏事,当然朋友做坏事的原因被理解为疯癫与心智失常 3.对于古代神话因为确实不够了解,也可以用欺妄做一个虚构与模拟 然后在书籍原文的这个382d部分左右讨论的是 神是否会变化欺骗人类的问题,而在后面讨论人事与城邦统治问题,再一次提出,进一步设计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可以欺妄,还进一步回答了谁、哪些人可以有欺骗权。如果把欺妄比作药剂,那惟有医生拥有治病的技艺,那么自然医生可以对病人撒谎(出于医生对事态的把握)而不是病人对医生撒谎。欺妄实实在在对于诸神是无用的,而对于凡人只有它作为一种药物使用时才是有用的,那么很明显,这种药剂必须交付在医生手里,普通人是不能接触它的
如果说能有什么人有权使用欺妄的话,那就是城邦的统治者了,后者,或是针对敌人或是针对市民,为了城邦的利益而使用欺妄;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权接触这样一件事物的
上面两段出在第三卷,最初那一段出在第二卷。上面两段主要协调城邦人事的问题,不涉及神。柏拉图要道明的是,惟有城邦统治者在真正基于城邦整体利益的时候,才有权动用欺妄权,除此之外城邦他人都不可对统治者欺妄,统治者也不可以出于私益而对城邦众人进行欺妄。 欺妄/谎言 具体在第三卷出现过典型实例,柏拉图为了协调城邦秩序,让哲人贤者统治城邦以及容斥各方的利益和改造他们的思想状态,根据赫西俄德的神话编造了 一个大家广为流传的灵魂分金银铜铁不同材质的谎言,人类思想史上最为高贵的一个谎言吧,其实柏拉图在这之前对欺妄的讨论或许本身就是为此高贵的谎言做的各种铺垫。不得不赞叹,《理想国》有点《红楼梦》的意思,草蛇千线、伏埋万里。关于那些影子,如果他被要求对他们进行估价和表示意见,并从而和那些用不脱离捆绑的人们发生争执,当他尚还处于黑暗中,两眼尚未适应和复原的时候,而这种适应和复原的时间是很不短的,是不是他将引起别人的讪笑,是不是人们将要议论他,说他走上去了一次却瞎了眼睛回来了,并且说试图往上走,这是根本不值得去的;而谁如果试图去解脱他们并且引导他们往上走,那就只要有人能够把他弄到手并且能够杀死他,他们就会把他杀死的?
这个申辩的相对显白段落还能够在稍后的325页查到眼睛上的混乱有两种,并且是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的,这就是:或者它们是从光亮中被转移到黑暗中,或者,是从黑暗中转入光亮中。正是这同样的情形,在灵魂上,相信也是一样。那么,一个人,如果他看到一个灵魂遇到困难了,它失去了观察和理解事物的能力,这个人不该无理地不智地去讪笑它,而是应该考察,这究竟是由于灵魂,从光明的生活中出来,因为不习惯而变得茫昧了,还是,从深刻的无助中出来,走进了一个更加光明的世界,它被耀眼的光辉窒息了;只有在这之后,他才能,去赞美和庆贺其中的一个灵魂曾经的经历和生活,而对于另一个灵魂表示怜悯,并且,如果他一定要讪笑它的话,他的讪笑,与讪笑那从上面的光亮中走出来的灵魂相比,也就不那么荒诞和可笑了
他们在灵魂里缺少任何光亮、明皙的模式,他们也不能,像一个画家睇视模像那样,睇视那最最真实的事物,并且永远,在超想着它那里的同时,把它当做为标准和鹄的,并且尽可能细微地一直观察到它的最细微、精确的细部,并而后,在此世,当需要建立的适合,去建立关于美、正义和善的事物的习俗和法则,而如果它们已经被建立了,那就严加护卫,而去保持和养护他们
那么不正义,是不是应该说这是那存在着的三个部分之间的冲突和内乱,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一种互相的干预和介入,是灵魂的某一个部分对于灵魂全体的暴乱,它企图在灵魂里建立一种与它不相称的统治,虽然按它的本性它本应是受奴役和听命于那个属于统治属类的部分的?正是这样的一些情形,我想,以及还有这些部分之间的混乱骚扰,它们的越轨失职,这些,我们要说,就是不正义,放荡恣纵,懦怯和无知,以及总起来一句话说,一切恶德。
亲爱的格劳康,这是一个巨大的斗争,这是一件大事,一件大于世人一般所以为的大事的大事,它涉及成为善还是恶,好还是坏;因此,一个人是既不能受名誉、财货,任何地位权势,并且同样,也不能受诗艺的怂恿唆使而忽略和无视正义以及其他的品德的
那些对于智慧和品德一无经验的,相反,对于饮宴酒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却总是贪得无厌的人,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朝底并又回过来朝向中间的人,并且一生都来回往复徜徉于一个区域之间,他们从来不会跨过和超越这一个区域抬眼去向着那真正的顶部看望,也不会去走向它,他们并没有被真实的“是”所真正地填充和给予满足,也并没有尝味过常住不变的、纯粹的快乐,相反,他们,按着牲畜的习惯,永远是两眼朝下,一头投向土地和食槽,不断地啮食,长肥育膘,交配繁殖,并且,为了整的对于所有这些的更大的满足,用铁的犄角和铁的蹄脚呼吸践踏,互相牴斗,互相杀戮,他们的欲壑难以填平,因为他们是试图用并不真实地‘是’的东西去填充和满足他们自身之中那个既不真实地“是”、也不能够持续盈足的部分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乃至这个版本对于“是”的翻译处理,在不同版本之间存有差异,“是”原来翻译为“存在和有”,对于“是”这个字学界前辈王太庆应该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个“是”与“存在”至少在字面意义上跟后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哲学有很直接的关联,他最著名的著作便是《存在与时间》即使他以什么方式接触到一点善的掠影,他也是根据意见,而不是通过知识去接触到的,并且在此时此刻的生母中醉生梦死,沉湎不醒,在他尚未在这个人世间苏醒之前,就将先行跌落到那个彼世的地府中去,最终地昏沉僵卧,永睡不醒了
塑造你们的神,对于你们之中凡是能够做统治者的人,在创造他们的适合,就用金和他们掺和在一起,并因此他们是最贵重的;对于助手或是卫士,就用银;而对于农人和其他手艺工人,就用铁和铜。由于你们都是同胞,因此,虽然就大部分情形来说,固然,你们所生育的子嗣都是与你们自己像的,但是也有的时候可以由金子的父亲生育出来银子的儿子,或由银子的父亲生育出来金子的儿子,以及其他的一切,也都可以这样地互相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