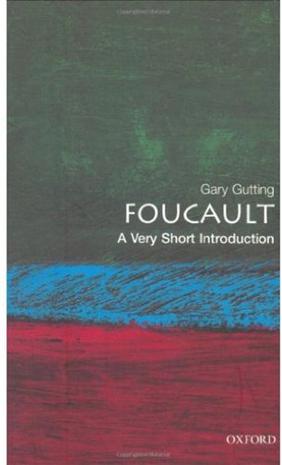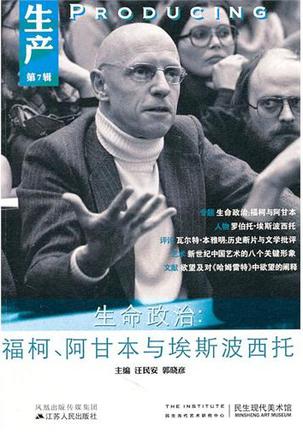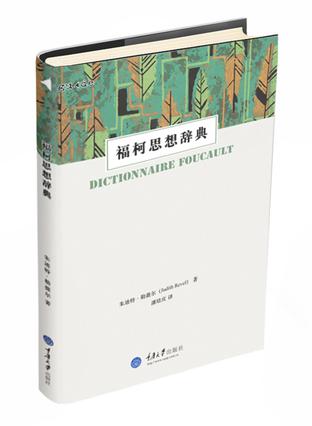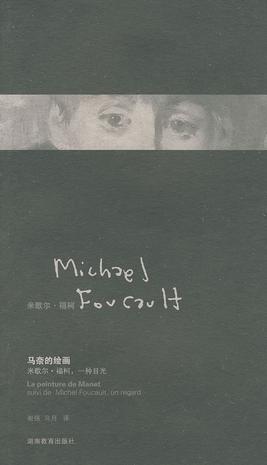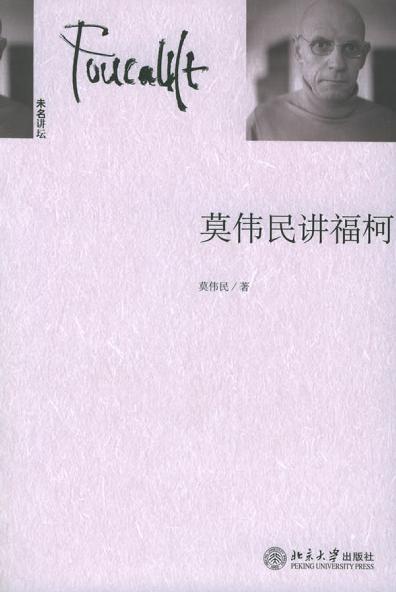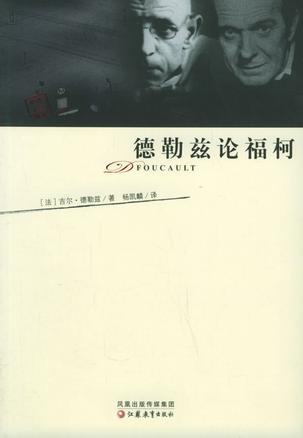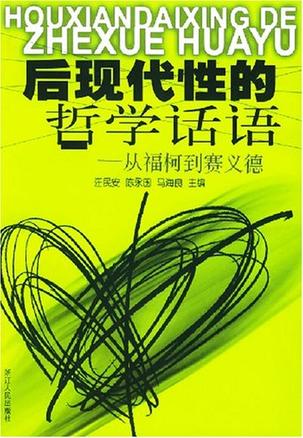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福柯
-
Foucault
Foucault is one of those rare philosophers who has become a cult figure. Born in 1926 in France,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ife he dabbled in drugs, politics, and the Paris SM scene, all whilst striving to understand the deep concepts of identity, knowledge, and power. From aesthetics to the penal system; from madness and civilisation to avant-garde literature, Foucault was happy to reject old models of thinking and replace them with versions that are still widely debated today. A major influence on Queer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 (he was openly gay and died of an AIDS-related illness in 1984), he also wrote on architecture, history, law, medicine,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of course philosophy, and even managed a best-seller in France on a book dedicated to the 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his arguments, people try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work have desperately sought introductory material that makes his theories clear and accessible for the beginner. Ideally suited for the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 series, Gary Gutting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but non-systematic treatment of some highlights of Foucault's life and thought. Beginning with a brief biography to set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ge, he then tackles Foucault's thoughts on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the avant-garde scene; his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work; his treatment 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modern society; and his thoughts on sexuality. -
生产(第7辑)
《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福柯、阿甘本与埃斯波西托》讲述了对于“生产”的关注,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正是在生产环节,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之后,“生产”获得更丰富的内涵:文化领域是知识生产,精神领域是欲望生产,政治领域是权力生产,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机器——而所谓“消费社会”不过是它的一个反讽性注释。“生产”,成为诊断当代社会的关键词。另一方面,“生产”这个词对于今日中国人而言似乎别具意味:我们曾经身陷“生产”之笼,如今,我们期待这个迷失在历史深处的词语重新获得活力。当然,词语自有其命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邀请。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生产”的内在语义,就是生成,流变,活力,它符合当代知识分子的气质: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是批判和思想的基本特征。 -
说真话的勇气
《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2)》是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两年的授课演讲,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治理”的续篇。在书中谈到“把所传授的、学到的、复述的、吸收的逻各斯变成行为主体的自发形式”。福柯不断地向前追寻直接表现在正值的行为和与自己的关系中的一种真实话语。他研究了政治的“parrhesia”,它被界定为真实的话语,不过是一种让说话者冒着拿他的生存作赌注的危险说出的真实话语。在书中,福柯有了令人惊讶的概念积累,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研究课题,以此走向“真理的通道”。 -
马克思与福柯
本书是法国9位重量级思想家重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文本,主要论述马克思在法国的传统,特别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 -
福柯思想辞典
编辑推荐 • 福柯常说,概念的配备,在严格意义上就是提供一个“工具箱”。然而,概念被制造出来、被固定下来,尔后它们还可能被抛弃、被修改,或者其含义被进一步扩大。概念就这样始终处于一种不断修补和移位的运动之中。这给《福柯思想辞典》的撰写计划提出了艰巨的挑战。 • 作者朱迪特•勒薇尔选择接受这一挑战。她用一种独特的编排方式,让这本《福柯思想辞典》清晰地呈现出福柯一生持续“提问”的主要路径。 • 哲学的任务不是解决问题,而在于“提问”。《福柯思想辞典》能够对福柯表示的最大敬意,即是它恢复了其思想中的提问方面。因此,《福柯思想辞典》并不是一本简单地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术语汇编,它的目的在于试图重建其连续的或相互重叠的众多提问,这些提问才是福柯分析中极其宝贵的财富。 内容简介 《福柯思想辞典》由近60个术语组成的“术语篇”和13个人名组成的“人物篇”构成。 在“术语篇”,作者既介绍了福柯从其他思想家那里借来的哲学概念,还介绍了福柯自创的前所未闻的概念。作者试图通过这些概念梳理,系统地勾画福柯的思路,以便使其哲学历程变得容易理解,同时顾及其经历的复杂性,其众多的分支部分和变化。 在“人物篇”,作者介绍了一些在福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思想家,包括巴塔耶、布朗肖、德勒兹、德里达、康德、尼采、萨特等。作者指出了他们之间的交汇点、论战的分歧、争论的领域或概念的借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福柯长达三十年的哲学和政治思考中,支配着其思想的既复杂又开放的过程。 最后,作者还加入了“福柯的著作目录”部分,以便读者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能够深入地追踪福柯思想中的某些线索。 -
必须保卫社会
《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勾勒出“惩戒”权力的一般草图,即通过惩罚机关的监视技术、规范性的制裁等,个别地运用于肉体的权力,从而勾画出“生命权力”的轮廓。福柯随后对“政府性”进行了追问,这个权力通过国家理性和警察的装置与技术,从16世纪开始运转。《必须保卫社会》完全可以成为当时权力的政治问题和种族的历史问题的相交点、会合处和联接点。 -
主体解释学
《主体解释学》内容简介:如果我是画家,要给福柯画一幅人物肖像,那我一定挺犯难的。因为福柯善变,在思想方面,尤其如此。这倒应了“人”一词的拉丁文原意,即“人”(persona)是透过(per)面具发出的声音(son),换言之,人是隔着面具说话的。综观福柯复杂多变的一生,他不仅如此,而且还不时变换着面具,发出不同的声音。 福柯是个腼腆的人,平日话不多,也不善交际。据说当年在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教书时,他与德勒兹、利奥塔等人都是同事,而且办公室也紧挨着,但是相互之间却绝少串门、聊天。其实,福柯喜静,爱呆在很少有读者光顾的索尔舒图书馆里查阅档案资料,读书与记笔记。有时疲劳了,他就出去遛大街,碰上熟人,也只是寒暄几句,然后又回去工作。这种工作狂的作风是巴黎高师培养出来的,它一度让少年福柯精神几近崩溃,两度试图自杀。 -
福柯的生存美学
本书厘清近年来流行于学术界的有关福柯思想的各种观点。但是,它又不是仅仅单纯论述福柯关于“权力”和“性”的观点,而是结合福柯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历程。全书系统完整、观点和思想富有创意,论证严谨细腻,行文深入浅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全面研究福柯思想的中文著作。 本书是一部全面而细致地阐述福柯思想的著作。作者试图厘清近年来流行于学术界的有关福柯思想的各种观点,使全书不是仅仅单纯论述福柯关于“权力”和“性”的观点,而是结合福柯本人的生活和思想变化历程。依据多年来福柯对其思想的自我诠释及其思想风格和写作风格,以生存美学为基本线索,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系谱学”、“真理游戏”、“生命政治”、“自身的技术”、“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等等和“生存美学”融会贯通在一起。重点凸显了福柯“关怀自身”的核心思想,并深入分析了“语言游戏的审美艺术”、“身体,性和爱情的美学”、“生话的技艺”、“老年生活和死亡的美学”等生存美学具体内容,阐明了生存美学的实践智慧性质及其彻底重构西方思想的典范意义。 在材料引证上,本书参照自1994年以来最新发表的福柯对话录、文集以及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录法文原稿,由此探索了福柯晚期所进行的生存荚学研究对于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贯穿性和总结性意义。全书系统完整、观点和思想富有创意,论证严谨细腻,行文深入浅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全面研究福柯思想的中文著作。 -
莫伟民讲福柯
本书只是讲解了福柯思想宝库的一个个侧面,但还是力求捕捉其哲学和史学等方面主要的侧面,避免给人以挂一漏万的感觉。同时,正因为这本书只选取了福柯多重思想的某些点、线和面,因而未曾涉猎之处和尚可完善之处也就会在作者面前敞开着,这就为作者以后进一步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尽管福柯倡导的“关切自身”的伦理学不禁让人联想中国儒家的修养性学说,尽管福柯思想所涉及的领域比较宽广,但无可否认福柯还是会有其知识盲点和无暇顾之处。正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一样会有局限,福柯才否认有什么普遍适用的真理,否认普遍知识分子具有普遍代言的作用。于是,福柯研究者和评论者无论是采取故意贬低还是刻意拔高的手法应该都是福柯所不愿看到的。既作为与真理相关的知识主体,又作为与权力场相关的权力主体,作为与苦行实践相关的伦理主体,真实的福柯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
德勒兹论福柯
时至今日,德勒兹与福柯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两则传奇。不读德勒兹的《德勒兹论福柯》,便不能说了解福柯。因为在德勒兹之后,福柯已不是原来的福柯,就如弗洛伊德在拉康之后,不再是原来的弗洛伊德一样。德勒兹与福柯这两颗法国思想界的熠熠红星在本书中一起迸放光芒,使福柯成为理解德勒兹的一扇重要窗口,使德勒兹成为透视福柯的不二法门。由福柯到德勒兹,再由德勒兹到福柯,两股思想之流不断地牵引、碰撞、发光与褶皱,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般奇诡景致。 -
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
1971年,那个政治和经济都起着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诺阿姆•乔姆斯基和米歇尔•福柯,两位在世界知识分子界处于顶尖地位的人,完成了一次堪称“世纪辩论”的交锋。这场辩论从“人的天性”出发,很快就拓展到了更宽泛的领域,涉及了历史、创造力、自由以及为政治正义所作的斗争。这本小书已经行销九个国家,也早已超出了学术图书的范畴,而这两位作者的知名度也超出了学术领域。 -
The Order of Things
When one defines order as a sorting of priorities, it becomes beautifully clear as to what Foucault is doing here. With virtuoso showmanship, he weaves an intensely complex history of thought. He dips into literature, art, economics and even biology in The Order of Things, possibly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yet most overlooked, work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clipsed by his later work on power and discourse, nonetheless it was The Order of Things that established Foucault's reputation as an intellectual giant. Pirouetting around the outer edge of language, Foucault unsettles the surface of literary writing. In describing the limitations of our usual taxonomies, he opens the door onto a whole new system of thought, one ripe with what he calls exotic charm. Intellectual pyrotechnics from the master of critical thinking, this book is crucial reading for those who wish to gain insight into that odd beast called Postmodernism, and a must for any fan of Foucault. -
福柯与酷儿理论
推荐这本书,心里颇有些矛盾:一方面,本来内容就有些单薄的小册子里居然有一半篇幅印着荒唐可笑的序言、前言、导读,这样的书还值得认真对待吗?可另一方面,关于福柯学说在英美同性恋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国内一直没有比较清晰的介绍。好歹这是第一本。最终,我想,只要其有一言可取,我们就不妨取其一言吧,至于此外的部分,干脆撕去算了。 此书最大的意义,也许还在于着重指出了女学者朱迪丝·巴特勒对福柯学说的深化和批判。巴特勒是当今性别研究和酷儿理论领域中最深刻的思想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比福柯更激进,比福柯走得更远。 -
不正常的人
在本书中,福柯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他认为“不正常的人”有三个源头,他们由历史上的三种人转变而来:一是“畸形人”,它不是指生理上有缺陷的人,而是对法律构成了障碍,使法律陷入困境的案例;二是“需要改造的人”,即某些桀骜不驯者,不服从管教,拒绝纪律的要求,等等;三是“手淫的儿童”,福柯认为,应从身体快乐原则出发,批判压抑理论,并将矛头指向对儿童的性进行干预的权力系统。 -
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本书是后现代性是六十年代以来由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推动的思想潮流。它对西方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总体性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同时也动摇了主体、理性、真理、语言、历史等概念的稳固的现代性内涵。最终,后现代性表现为一种祛伪式的哲学形式和知识形式。本书收录的是后现代理论中堪称经典的文献,正是这些理论家及其著述,刻写了后现代进程中无法抹擦的痕迹。 -
福柯-牛津通识读本
《福柯》由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加里•古廷撰写,在很小的篇幅内对福柯作出了精彩的解说,为这位深奥的哲学家那复杂丰富的思想提供了导航。清华大学教授、福柯研究学者刘北成作序推荐。 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的作品对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涉及面广与影响力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以晦涩难读著称。本书为福柯的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导读,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作者加里•古廷还探究了一些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在福柯深入研究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领域时,曾让他甚为着迷。 -
临床医学的诞生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
Discipline and Punish
In the middle ages there were gaols and dungeons, but punishment was for the most part a spectacle. The economic changes and growing popular dissen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ade necessary a more systematic control over 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society, and this in effect meant a change from punishment, which chastised the body, to reform, which touched the soul. Foucault shows in fascinating detai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system of prisons, police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hierarchies of social control --- and the growth of disciplinary society as a whole. He also reveals tha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 school and a prison is not purely facetious --- prisons, schools, factories, barracks and hospitals all share a common organization, i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control the use of an individual's time and space hour by hour.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