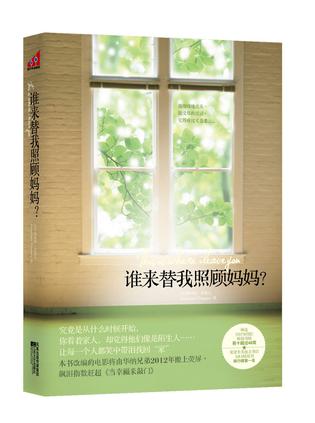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我慢慢的点头,接受你的谎言,觉得难过又苍
-
谁来替我照顾妈妈?
福克斯曼先生过世了,他的儿女们,在母亲的严肃谎言下,用各种各样啼笑皆非的形式纪念他,包括在教堂里抽大麻、在守灵时大打出手,毁掉情敌的名车…… 福克斯曼家因不会正确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渐行渐远的兄弟姐妹,通过为父亲守丧七天的相处、冲突甚至“狼狈为奸”,找到了彼此疏远的原因和再次亲近的方法,找回了童年时亲近的感觉,找回了他们心目中的家人…… 谁来替我照顾妈妈?这本书是强纳森·崔普尔2009年出的一本小说,当时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后来华纳兄弟以天价签下本书,将这本书带来的风暴推上高潮。强纳森·崔普尔非常擅长写坏男人、家庭危机等,他总是用非常幽默辛辣的语言、明快的风格去描绘在众人眼中看起来很不愉快的现实生活,让人们感受颇深,但是却从不给人们带去消极的东西,也就是人们在阅读他的书时会有极舒服的感受,而非感到阴暗与纠结。 本书将改编为电影,导演为格里格·伯兰蒂。格里格·伯兰蒂是一位美国电视剧界的金牌制作人,他曾编剧、制作了《罪恶财富》(Dirty Sexy Money)、《兄弟姐妹》(Brothers & Sisters)等,他最近一次执导电影电影数十部,其中《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及电视剧《兄弟姐妹》(Brothers & Sisters)在国内积攒了不少的人气。也相信,《谁来替我照顾妈妈?》将会成就他另外的事业高潮。 精彩书摘1 贝蒂的女儿汉纳去年离婚了。”我妈兴致勃勃地说,好像在发布一个特别好的 消息。 “真令人难过。”我说。 贝蒂点点头,“他沉迷于网络色情。” “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我说。 “贾德的老婆给他戴绿帽子。” “妈!” “干吗?有什么好丢脸的。” 贝蒂和我妈两人相视而笑,像在密谋什么事,我还可以听见她们之间心电感应的电波声。她老公沉迷于网络色情,他老婆跟别的男人乱搞……真是完美组合! “我还不打算这么快开始交女朋友。”我说。 “又没有人叫你去约会。”我妈说。 “对啊,只是打通电话,不然就喝杯咖啡。”贝蒂说。 她们两个满怀希望地看着我。我感觉到菲利普的手肘在顶我的肋骨,他在窃笑。这种日子我还要再过六天,如果不趁早让她们死了这条心,我妈会把我的情况广播给整个小区知道。 “问题是,我自己有时候也很喜欢一些不错的网络色情图片。”我说。 “贾德!”我妈倒抽了一口气,一脸惊恐。 “有些做得还蛮有质感的,尤其是现在我又单身,这个资源还不错。” 菲利普突然扑哧大笑,贝蒂·艾里森满脸通红,我妈则是跌坐回椅子,一脸被打败的样子。汉纳·艾里森和她的两个名字,都从板子上除去了。 序言 爸走了,”温迪漫不经心地说,好像这是曾经发生过或每天都会发生的事。这种就算悲剧当前,她也能处变不惊的样子,真的会让人郁闷。“两个小时前走的。” “妈还好吗?” “她是我们的妈妈,你知道吧?她更想知道要给验尸官多少钱。” 发生重大事件时,我的家人向来无法正确表达情绪,这让我觉得很火大,但听到这句话我还是笑了。没有哪一个庄严隆重的场合,我们福克斯曼家不是用快闪或讽刺的话逃避的。这是我们家的正字标记,我们的基因就是如此。不管是生日、假日、喜宴还是去探病,我们都用嘲讽、双关语和取笑的方式表达情感,现在就连我们的父亲过世了,温迪还是有兴致耍嘴皮。用这种方式悼念父亲倒也很适合,因为说到用这种方式表现内心压抑的情感,他可是前辈。 “这样好多了。”温迪说。 “好多了?天啊,温迪,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好啦,这样说不对。” “你真这么想?” “他要我们照犹太人的习俗为他服丧七天。” “谁说的?” “我们在谈谁?当然是爸啊!爸要我们服丧。” “爸走了啊。” 温迪叹了口气,仿佛要穿过我这片浓密的驽钝丛林让她精疲力竭。“是啊,所以现在显然就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时候。” “但爸是无神论者。” “爸以前是无神论者。” “你是说他过世前发现了上帝?” “不是,我是说他过世了,你应该跟着改变动词时态。” 如果我们听起来像两个冷血的混蛋,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但其实,打从爸爸一年半前就被诊断出有问题以来,我们已经断断续续哀伤了一阵子。他本来就有胃痛的老毛病,但一直不理会我妈的请求,不愿去医院看病,只是一味增加已服用多年的胃药剂量。他把这些药看成救命仙丹一样地吞,不论到哪里,总是随手丢下几个药片的铝箔包装,所以地毯看起来像刚铺好的人行道一样闪闪发光。后来,他的粪便就变成了红色的。 “你爸觉得不太舒服。”老妈在电话中总是说得轻描淡写。 “我的大便流血了啦。”爸爸在老妈后面抱怨。我搬离家这十五年来,爸爸从没接过电话,一直都是妈妈来接,而他在旁边找适当时机插话,发表几段怪里怪气的评论。这很像他的人生,老妈永远在舞台中央,娶她就像加入合唱团。 透过计算机断层扫描,可以看到爸爸的肿瘤像朵花,盛开在他深灰色的十二指肠壁上。翻开爸爸默默忍受痛苦的传奇史,还会再找到一则故事,讲的是他花了一年用胃药治疗转移性胃癌。这个过程里有预料中的手术、放射线治疗,然后就是无止尽的化疗,希望能缩小他的肿瘤,但被缩小的反而是他。他曾经宽阔的肩膀,最后瘦到只剩关节,肩膀好像就这么从他松垮的皮肤下消失;接下来是肌肉和肌腱逐渐萎缩,然后是极度疼痛,最后陷入昏迷,而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再醒过来。不过他为何要醒来?为何要醒过来面对胃癌末期的痛苦折磨? 从他昏迷到过世大约四个月,比肿瘤科医生预估的还多了三个多月。我们去请教医生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父亲是个战士。”但这句话很没有意义,因为他已经活生生被病魔斗垮。如果还有知觉的话,他一定会很生气,像死亡这么简单的事,竟然花了他这么久的时间完成。爸不相信有上帝,但他终生信奉“别占着茅坑不拉屎教”。 所以“他真正过世了”这件事本身,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最后的悲伤细节。 温迪说:“丧礼明天早上举行,我今晚就会带孩子过去。巴利在旧金山开会,他会连夜搭飞机赶过去。” 温迪的丈夫巴利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人。据我所知,他们公司花钱让他搭私人专机,到世界各地陪有钱人打高尔夫球,但他多半是输球给这些可能需要他的基金赚钱的客户。几年前公司调他去洛杉矶办公室,其实这完全没道理,因为他本来就经常飞来飞去。而温迪当然比较喜欢住在东岸,因为在这里,她肿胀的脚踝和产后赘肉的负担比较轻。至少,这些不方便在平均肥胖度较高的东岸,可以得到不错的心理补偿。 “你要带小孩来?” “相信我,我宁愿不要,但让保姆带他们七天太久了。” 她的小孩一个叫莱恩,六岁;一个是科尔,三岁。这两个小男生都有一头淡黄色头发、天使般圆润的脸颊,不过还没有哪个房间能让他们待两分钟还不被搞乱的。温迪还有一个女儿瑟琳娜,才七个月大。 “七天?” “服丧就是要这么久。” “我们不会这么做,对吧?” 温迪说:“这是他的遗愿。”有那么一瞬,我想我可能听到了她喉咙深处发出的悲伤声音。 “保罗也赞成吗?” “就是保罗告诉我这件事的。” “他怎么说?” “他说爸要我们服丧。” 保罗是我哥,比我大十六个月。我妈坚称我的出生并不是个错误,生完保罗七个月后又怀孕,完全是她故意的。但我从来不相信,尤其是爸爸在一个周五晚餐上喝了桃子酒,闷闷不乐地承认,那时候他们不相信哺乳时还能怀孕后。保罗和我的感情倒还不错——只要我们不聚在一起。 “有人告诉菲利普了吗?”我问。 “我已经在他最后让人知道的手机里留言。假设我们运气不错,他听到了留言,也正好没在监狱或没有死在臭水沟旁,那就有理由相信他有一点点可能会出现。” 菲利普是我们最小的弟弟,比我晚九年出生。实在很难理解我父母生小孩的逻辑,温迪、保罗和我都相差不到四岁,菲利普则是快十年后才报到,像一个不协调的尾音突然“啪”一声出现。他在我们家就像“披头四”乐团里的保罗·麦卡尼,外貌比其他人出色,拍照时永远和其他人看不同方向,偶尔会有谣言说他已不在人世。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不是被骄纵就是被忽略,或许这就是他长大后什么事都会搞砸的原因。 他现在住在曼哈顿,他经常从定位系统上消失好几个月,然后有一天突然不请自来地出现在你家门口,和你共进晚餐。偶尔会提一下他进了牢里,或者去了西藏,不然就是刚和某个要红不红的女演员分手。我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他。 “希望他能来,”我说,“如果没来,他会良心不安。” “说到我命运多舛的小弟们,你自己的希腊悲剧如何了?” 温迪说话麻辣、不怕得罪人的样子很有趣,甚至接近迷人的程度,但如果粗鲁和残忍之间有道界线的话,我想她从来没注意过。通常我还能欣然接受她这样挖苦我,但这几个月来我身心俱疲,所有防卫能力消失殆尽。 “我要挂电话了。”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不像是个快要崩溃的男人。 “贾德,我只是要表达我的关心。” “我确定你是这么以为的。” “噢,少来以退为进这招。我已经受够巴利这样对我。” “那就家里见。” “很好,那你就继续这样下去,”她不悦地说,“再见。” 我等她先挂电话。 “你还在听吗?”她最后终于说了。 “没有。”我挂断电话,想象她边甩上电话,边机关枪似的从嘴唇间射出连珠炮似的咒骂。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