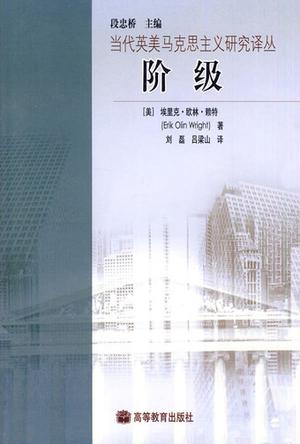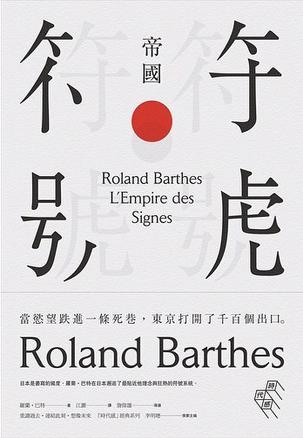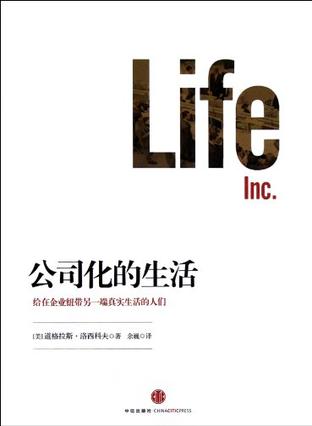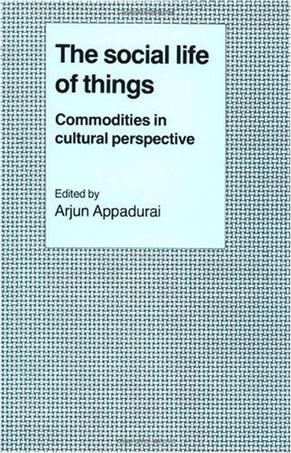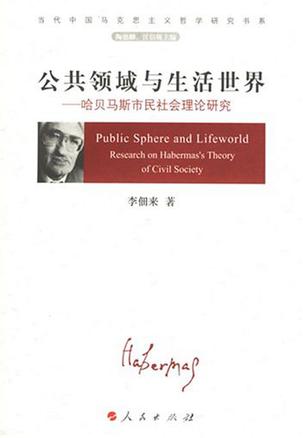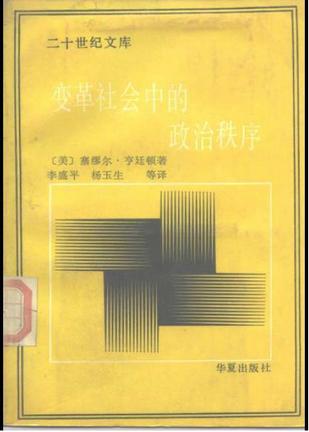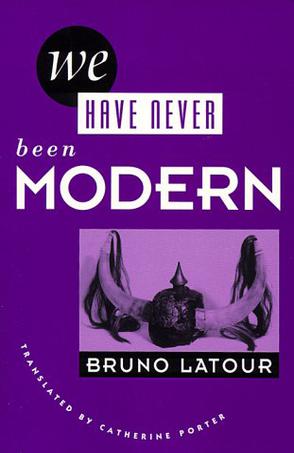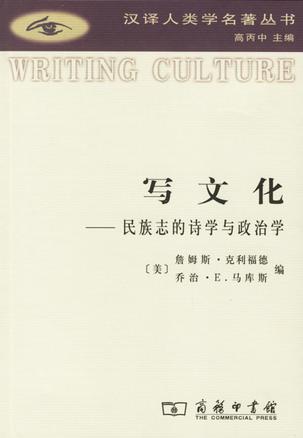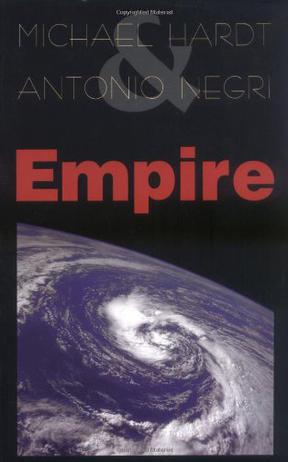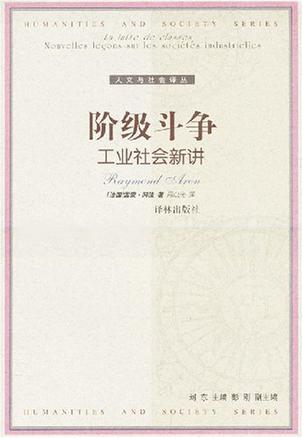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社会学
-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本书通过研究佛教这一东方主要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现象,比较研究了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的不同思维方法。 -
韦伯作品集XI:古犹太教
《古犹太教》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研究古犹太教都是从宗教学的角度,以文献考证来看待古犹太民族与现代基督教的关系,而韦伯则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把古犹太教放在西方和近东整个文化发展交汇点上审视这一宗教历史的内在理路,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对立宗教文明盘根错节的难解因由。 -
阶级
在这一开创性的新著中,埃里克·欧林·赖特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概念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重建。《阶级》为阶级的抽象结构概念和对特定历史环境中阶级角色的描述之间的断裂搭起了一座桥梁。它将剥削概念恢复为阶级分析的核心,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容纳了中间阶级的经验复杂性,也涵盖了国家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的存在性。论证有力,逻辑简洁,文笔清晰,这些优点使得《阶级》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文献。 -
社会因何要异见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从众常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导致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鉴于此,本书专门讨论从众之危害,以及异见之重要。 作者简介 -
歧视经济学
加里·贝克尔对于歧视问题产生兴趣,起因是二次大战以来,歧视弱势群体者的议题,其篇幅在美国的报纸所占份量最多,尤其是歧视黑人这种事。这些议题虽然大多数涉及上教堂、上学和投票等非市场的活动,但也相当多的讨论涉及市场,贝克认为,市场歧视不只直接影响经济,间接更波及非市场范畴。 《歧视经济学》共分十章,先将重要定义和基本方法在第一章说明,接着第二章引用国际贸易理论详估歧视效果,第三章则讨论雇主歧视,第四章为受雇者歧视,第五章讨论消费者和政府歧视,第六章则建立一个综合讨论三~五章所剖析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效果之理论模式,七~九章是对实际现象的应用,最后一章是结论。 -
符號帝國
當欲望跌進一條死巷,東京打開了千百個出口。 一九七○年,巴特宣稱日本將是符號產製與消費的終極國度。 如今,將此書置於日本戰後重新崛起、各類商品風行全球的脈絡, 會發現巴特或許無心插柳,卻極為精準地預言了日本當代文化經濟的核心構成: 操作符號、製造意義、深植人心。 這對與日本有著深刻複雜關係的我們來說, 正是重新探究日本有別於歐美、「另類現代性」的一個閱讀起點。 日本是書寫的國度, 羅蘭.巴特在日本邂逅了最貼近他理念與狂熱的符號系統。 日本最能遠離西方符號驅力在我身上引發的一切厭惡、惱怒、拒斥。日本的符號很強烈:令人激賞地井然有序、安排得宜、標示清晰,保有自主,從不西化或理性化。日本的符號是空的:它的符徵逃逸了,在這些無償支配一切的符徵深處,無神、無真理、無道德意義。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到處揭示著這種符號呈現出來的優越特質、高尚的自我肯定及情欲魅力,一切表露在物品及最微不足道的舉止(那些我們通常視為毫無意義或庸鄙不堪的行為)之中。因此,符號場域將不會透過它的制度面來探求:重點不在於藝術、民間傳說,甚至是「文明」(我們不會將封建日本與現代科技的日本互為對比)。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都市、商店、戲劇、禮儀、庭園、暴力;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幾個動作、幾道菜、幾首詩;我們要探索的主題,是臉孔、眼睛,還有畫筆。這一切,乃是運筆寫下,而非畫下來的。——羅蘭.巴特 -
公司化的生活
在所有人的生活背后,都有许多间有限公司。 企业已经让人们与生活的真实意义渐行渐远。 如何面对公司对我们生活的掌控? 在所有人的生活背后,都有许多间有限公司。真是面对全球化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现实下,对人生最贴切不过的描述。《公司化生活》回顾了500年以来的商业社会发展,几个世纪以来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把我们的世界转变成一个个人之间彼此较量的世界。企业已经让人们与生活的真实意义渐行渐远。 书中追溯商团主义(corporatism )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萌芽,回看今日社会无不处于公司、集团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思考欧洲古代各种职业行会演变至垄断及跨国集团的进程。 面对公司对我们生活的掌控,作者认为解决之道其实也很简单:既然公司、商品及广告将我们与真实社会隔绝,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关心社会和身边的社群,多读社会专题的期刊,重新接触真实的人们和物事。这样做,也许还能在全球化世代中保持头脑清醒。 -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The meaning that people attribute to things necessarily derives from human transactions and motivations, particularly from how those things are used and circulated.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volume examine how things are sold and traded in a variet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ettings, both present and past. Focusing on culturally defined aspects of exchange and socially regulated processes of circulation, the essays illuminate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find value in things and things give value to social relations. By looking at things as if they lead social lives, the authors provide a new way to understand how value is externalized and sought after. They discuss a wide range of goods - from oriental carpets to human relics - to reveal both that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everyday economic life is not so far removed from that which explains the circulation of exotica, a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economies and simpler, more distant ones is less obvious than has been thought. As the editor argues in his introduction, beneath the seeming infinitude of human wants, and the apparent multiplicity of material forms, there in fact lie complex, but specific, soci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that regulate taste, trade, and desire. Containing contributions from American and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he volume bridges the disciplines of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and marks a major ste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basis of economic life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It will appeal to anthropologists, social historians, economists.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of art. -
学术的秩序
本书探讨的是教育问题。本书就是在希尔斯过世后,由他的几个弟子从他有关论述高等教育的若干论文中选编辑成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还算不上是一部专著,只是一本论文集,希尔斯好像也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专著。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38年,最晚的发表于1995年(希尔斯在这一年辞世),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仅仅是一本书,它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学家的希尔斯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
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本书依据丰富的文本资料,详细讨论了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背景和演变过程、问题领域和概念框架、理论特点和急论要点,深入分析了这一理论在当代思想界中的重要学术效应,并对其价值与限度作出了全面的定位。在书中,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公共领域理论为基本话语背景,第二阶段以生活世界学说为主要构架平台。这种概念不仅内含社会结构之界分、合法性之论证以及民主之阐说等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主题,也与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理论勾连在一起。因此,公共领域、生活世界、社会批判、市民社会以及现代性等表面看似并不相关的问题,在本书的讨论中却得到了内在的统一。 -
斗争的动力
本书选取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18例斗争事件,试图通过比较性的分析,为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各类政治斗争事件提出一个较具一般性的方案。几位作者详细说明了他们在解释革命、民族主义及民主化问题时所使用方法的含义,力图辨明一再引发广泛的斗争政治活动的各种机制及其作用过程,如居间联络、范畴形成和精英背叛等等,由此对目前斗争政治研究领域盛行的静态的单一行动者模式提出批判,并将分析的重心转移到斗争中的动态互动上。 -
历史、身体、国家
这本书基本上想要回答三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怎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对这些问题的质疑与回答构成了本书的基本论调。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讨论来澄清,身体的存在和意义是怎样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因随着国家民族命运的更动而被积淀、塑造出来?这本书以四个议题来证明揭示身体在近代中国的变化。它们分别是: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空间化发展。 在身体的国家化发展方面,作者以出现在清末民初的系列国民改造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体制改变,来省察身体的国族化发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探讨的是,近代中国的法系由旧有的伦理法演变为权利法时,身体的发展和建构在其中经历了什么变化。 这种改变对独立的身体和国家民族化的身体建构有什么作用?至于在时间化方面,作者论证“世界时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侵入中国,对中国的身体所造成的关键影响。而在空间化方面,作者以清末民初的学生运动为例,以游移在街道和公共广场上的身体来检视身体的建构与空间的关联。 通过这些讨论,作者希望呈显一个图像,那就是身体的生成其实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与结果。这种为了国家,以及经由国家,而形成的身体认知方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世事的演变而消减,相反地,它正以强势的态度主导着当代中国的身体发展。这本书的撰写就是想要开启一道门,让我们一窥这种偏狭发展的危险。 -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With the rise of science, we moderns believe, the world changed irrevocably, separating us forever from our primitive, premodern ancestors. But if we were to let go of this fond conviction, Bruno Latour asks, what would the world look like? His book, an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shows us how much of modernity is actually a matter of faith.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modern? What difference do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ke? The difference, Latour explains, is in our careful distinc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between human and thing, distinctions that our benighted ancestors, in their world of alchemy, astrology, and phrenology, never made. But alongside this purifying practice that defines modernity, there exists another seemingly contrary one: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that mix politic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nature. The ozone debate is such a hybrid, in Latour's analysis, as are global warming, deforestation, even the idea of black holes. As these hybrids proliferate, the prospect of keeping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ir separate mental chambers becomes overwhelming--and rather than try, Latour suggests, we should rethink our distinctions, rethink the defini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itself. His book offers a new explanation of science that finally recogniz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and so, between our culture and others, past and present. Nothing short of a reworking of our mental landscape.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blurs the boundaries among science,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 on all sides. A summation of the work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rovocative interpreters of science, it aims at saving what is good and valuable in modernity and replacing the rest with a broader, fairer, and finer sense of possibility. -
写文化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宣传与公共意识
本文集所译介的几部著作分别成书于不同时期,均为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基本上涵盖了作者政治理论的核心体系,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进而对当今世界的最大热点问题之一——恐怖主义——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有助于国内学人及广大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政策。 -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
《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知识与社会译丛》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简洁明快的笔调,通过概括叙述科学史上的重要发现的社会维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同时,也把作者基本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体现了出来。读者不权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和启发,而且能够"按图索骥",进一步开展自己的研究和探讨。我们今天具有的、来源于先贤的科学知识,当时究竟是怎样从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炮制出来的?这样的“炮制”过程对科学知识产生了什么影响? -
阶级斗争
简介: 雷蒙·阿隆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与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后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因此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前 言 1962年,当我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的时候,我写了如下一段话:“这些课事实上是于1955至1956年间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曾由大学文献中心把授课内容用速印机油印出来。直到今天我仍拒绝把讲稿原封不动地出示给更广泛的读者。我把我迟疑的理由立即告诉读者。这些课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研究的机会,是学习的工具,它们启发一种研究方法,勾画出一些概念,提供一些现象和见解。讲义中保留着而且不可能不保留讲课和即席发挥的痕迹。这些课程事先没有撰写成文,因而是口语形式的,难免有缺陷,事后尽管做了修改,以减少其不足之处,但不可能彻底消除。” 《十八讲》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国外多家出版社表示要将它翻译出版,这促使我决定发表这第二册书,然而我仍然要重申关于前面那本书所做的提醒。本书的十九讲是于1956至1957年间在巴黎大学教授的课程。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虽然对阶级斗争的分析本身是自成体系的,但是读者只有把两册书看做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才能充分抓住分析的依据和意义。我对工业社会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曾使一些评论家感到意外的把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进行对照的做法,在我看来都将因研究的展开而得到证实。对于工业社会的研究本身不是终结,它应该作为先导,引入另一项研究,即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的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的内容。 同时,我很愿意用几句话来回答某些评论家对我的一个指责,应当说他们是出于好意,如米歇尔·科利内和罗贝尔·康泰。为什么我没有把本属于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东西,即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和用语,归于他们的名下?如果我意欲对这个概念做一个历史性的概述,显而易见,我必然会去参照圣西门主义者或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如同我在其他情况下已经做的那样。然而这不是我在《十八讲》中前四讲所要表述的意图,在那里我仅仅想粗线条地勾勒我打算遵循的方法,同时我也想提出把托克维尔预见的逐渐资产阶级化和马克思预言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两者进行比照。关于托克维尔既不是理论家又不是工业社会(在他所访问的美国当时尚不存在工业社会)的目击者这一点我很难不知晓,尽管米歇尔·科利内煞费苦心让我明白。但托克维尔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未来社会的见解比马克思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的看法要更加正确,本书要证实的正是这个事实,如果不是坐井观天地看待西方社会,所确认的也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决定了我选择上一个世纪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并展现他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为的是将它们与本世纪的现实进行比较。 把圣西门主义者阐述的题材与现实加以对照也并非没有好处和教益。我在论述有关战争的主题时正是这样做的,我引证了奥古斯特·孔德。然而当涉及圣西门主义者时,会出现两类困难:如同亨利·古耶在一些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亨利·德·圣西门本人的思想在圣西门主义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难以将奥古斯丹·蒂埃里、奥古斯特·孔德、昂方坦和巴扎尔的贡献与圣西门主义割裂,虽然某些人对此故作不知,但任何人都未予以否认。圣西门主义者表达和传播了时兴的思想,与时代精神相呼应,他们的思潮缺乏严谨和系统的形式。托克维尔或马克思分别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而我们也许不能对圣西门主义者作出同样的评价。 当然,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能够称得上是我们所生活的技术社会的预言者,如今,在电子机器尚未管理我们这个社会之时,经理阶层管理着这个社会。但是他们在预示所有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时,却无视我们时代经历大分裂的可能性,这两册书(继而第三册)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力图客观地来讨论这个主题。托克维尔设想民主社会可能具有两种体制,一种是自由社会,另一种是专制社会。卡尔·马克思则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分别以这两个阶级所统治的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圣西门主义者和奥古斯特·孔德对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更缺乏判断力。或者至少是这样:假设某一天对事物的管理应该取代对人的统治,那么为使圣西门主义者和崇拜奥古斯特·孔德的人得到安慰,我们也只能说他们的预言还是大大地超前于今天的社会。 讲课距今已有六年多。最近十五年西欧历史发展之迅速令人震惊,使我今天不可能完全像昨天那样来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在我看来这项研究的成果已为世事的演变所证实。但是在某些要点上还需加以补充,在这个前言中,我将只是扼要地予以指出来。 一,工人阶级是越来越走向趋同,还是正相反,即越来越走向分化?分化的原因是工人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有些是没有任何专业资格的非技术工人,有些是持有专业培训文凭的工人或管理着一架机器的低级技术人员。我认为我给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充分的。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没有价值,因为多种多样和互相矛盾的演变是纵横交错的。上一个世纪所有工业部门中的专业人员失去了他们的重要地位,此外,众多工业部门中的熟练工人似乎销声匿迹而成为毫无特色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被迫从事一项“分割得极细的劳动”。但是这种景象仅代表所有工业组织类型中的一种,在某些尖端工业部门(石油、电子、电气)中,工业组织类型好像完全不同。从新型工人阶级的情况看,一方面是不同的劳动组织形式,另一方面是更高的消费水平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这种作用将逐渐窒息上世纪可能存在的工人团体的原始文化和自主文化)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两种简单说法——日益增长的趋同,日益增长的分化——中的任何一种都不符合现实的复杂性。 二,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使阶级斗争具有政治色彩,换言之,无产阶级要把自身定位于一个旨在全面夺取政权的政党,这些都不再时兴,甚至在共产党保有稳固的常设机构和几百万选民的法国或意大利都如此。在意大利,共产党寻求一种更灵活的策略,并拒绝全盘谴责共同市场。经验甚至使最狂热的思想家都几乎不再坚持认为:在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合适地把工会和政党旨在进行即时的改革(列宁依据英国的范例称之为工联主义)称做实用主义的活动,而把共产党反对现存制度和以革命为目标称做意识形态活动的话,那么,十五年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处处都加强了实用主义趋势,而削弱了意识形态趋势。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冲突从此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利益分享”,那就错了,因为增加工资或抵制技术改造会引起痛苦的转化过程。尽管眼下在大部分国家中的大部分工人似乎对共同管理的种种方式还有点漠不关心,但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在某些国家,以组建企业为目标的请愿将发展起来。在实用主义争论和意识形态冲突之间,人们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论战或斗争,其最终目的可能是加强劳动者参与企业生活,或者加强管理人员或劳动者代表参与某方面的领导。 三,最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居民的生活水平继续在提高,与此同时,一部分居民——有人说占20%到25%,另一些人说占15%到20%——的贫困状况没有消失,相对地说,也许绝对地说,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这种现象在美国比在西欧国家更为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保障的缓慢进程(老年人的贫困)、多种族的并存(黑人、波多黎各人)、悬殊的地区差异(某些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青年的失业现象等。富足社会中“失败者”的分量不均衡地落到各类社会集团的身上。最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最可能找不到职业。 尽管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不那么突出,目前,欧洲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阶段,但时过境迁,同样的问题也有可能在这里显露出来。现代企业技术复杂,要求为数更多的劳动者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准。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提供给最缺乏专业知识的劳动者,即使被雇用,他们从工业社会感受到的也只是受奴役而非得益。 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贫困问题甚至赤贫问题正显现出来。这里所指的贫困不是在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下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问题。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贫困化概念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是贫困问题并不因此就不存在,它恰好提醒那些素来易忘记它的人,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不是达到社会稳定和建立真正人道主义关系的灵丹妙药。劳动能够创造数量日益增加的财富,使得造成上世纪被人们称为社会问题的依据发生变化。现在更重要蹬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改变对现有财富的分配方法。然而,一味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技术进步都不能担保会带来公正的秩序,更谈不上保证出现符合人类所向往的生活条件,人类为此而改造世界,甚于对自身的改造。 许多读者从《十八讲》中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按人们通常理解的含义讲,这个结论或者由于它极平凡而被认为是明摆的事实,或者被看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一切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呈现相似的特征,一本苏联杂志竭力对我进行的辱骂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力求明确指出苏联式经济和西方式经济间对立的真实本质。在双方的科学和生产技术都相同的情况下,在两种经济模式或增长模式之间,在两种类型的工业社会之间作比较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得出这个推断,无需成为像莫斯科的批评家们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说这两种制度具有相似性并不意味着——那些在苏联《文学报》上反驳我的人可以放心——能够贬低两者的区别。即使比政治制度差异更小的经济制度,其区别也足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行斗争”。斯大林的经济制度和赫鲁晓夫的经济制度都不允许我们要捍卫的政治自由存在。 但愿有一天,这些差异会缩小,两个世界将不仅像今天一样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是不互相摧毁,而且意识到它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热切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但是只要和平共处即理智地拒绝热核战争,尚未变成思想意识共处,也就是说,尚未承认对方的存在权利,尚未停止宣称自己掌握着惟一和绝对的真理,只要论战的目的仅仅是在于使用什么最有效的方法以清除所有不赞同越来越过时思想的人,那么,对于制度进行的比较社会学研究将依然是学院式的习作,而不是历史性的对话。但是学院式习作有时已为历史性对话做了准备,也许正在热闹的宣传声中悄悄地成为历史性对话的真正组成部分。 1963年8月于布拉奈 附 录 一些批评家责备我没有整理出《十八讲》中的统计数字。由于课程的本身特点,我对这些责难并不在乎。从任何方面看,课程不是对俄国或美国社会、苏联式或西方式社会的描绘。课程的意向是得出一些基本概念、检验一种分析方法、消除幻想或成见。当前五年计划完成的确切程度、苏联和美国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我们研究最需要的内容,尽管这些事实或这样的比较值得关注。 然而为了满足某些读者的好奇心,另外也是因为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提出了一些在课程中几乎没有指出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附录中提供一些补充信息和最近统计材料是有益的。 1950年到1960年期间,西欧的增长率不仅远远高于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的增长率,而且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曾经计算出的增长率。法国在1950年到1960年间,生产力人均年增长率在农业中为4.7%,在工业中为4.5%,在服务业中为3.3%。德国和意大利在1949年到1959年间的增长率更高一些:德国的农业和工业都为5.6%,意大利的农业和工业各为5.4%和7.1%。美国相应部门的增长率为3.8%和3.7%,英国为3.9%和2.1%。 1960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63%,如果加权参照法国价格,该比例则为47%。假定国民总产量的增长率是4.7%,到1985年,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如果参照美国价格加权,将相当于当前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2%,如果参照欧洲价格加权,该比例为115%。如果五十年代的法国增长率持续不变,而且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长期保持稍低于2%的增长率,人们显然可从中得出结论,二三十年以后的法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于美国。所有这些计算都建立在一种传统的方法上。人们首先确定劳动力总数,人们接受某个生产增长率,接受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对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中的一定分配,同时接受按不同收入水平对劳动力最终需求的一定分配。最先进的国家把劳动力的分配及其最终需求量作为参照。这些数值尽管投射出巨大的不确定范围,但意味着从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消费增加2.5倍。因而198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以1959年的价格衡量将在9100法郎上下,相当于三口的中等家庭每月2300法郎。工业产量将始终在全部产量中占主要部分,即总产量的三分之二。45%的人口将在服务业工作。 即使西欧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于美国,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而言,美国继续比旧大陆发展得快,因为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8%,比法国或德国高得多(两者都低于1%)。此外,美国幅员辽阔——这是英国和德国都无可比拟的。 这些数字提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否由于不可能保持或不可能再现的增长原因,五十年代的增长率是例外情况?或者是否这个增长率预示了西方经济真正的质的变化?由于统计和方法的不确定性,不同作者计算出的比率有差距(尤其是人们应该取哪种价格作参照,是最初年份、最终年份还是中间年份的价格?),但无论差距大小,所有作者在大约的数字上意见都一致。从1839年开始算起,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实际价值)年增长率为1.58%,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5%。没有出现人均增长率增加或减少的明显倾向,因为总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根据人口增长率必然有增长或减少的倾向。 另一篇由D.C.佩奇、F.T.布莱卡比、S.弗罗因德写的论文(也发表在《工业经济社会研究及资料学会学报》上,第804期,1961年12月1日)按每人每年创造的实际价值(换个说法是一年期间每个劳动者的生产率)计算出国民生产的增长率。对长期增长率的计算,日本自1880年起,意大利自1863年起,德国自1853年起,法国自1855年起,美国自1871年起,英国自1857年起,结果如下:日本最高,约为2.9%;英国和意大利最低,约为1.2%;美国以2%的比率位居西方国家之首;德国和法国为1.5%。如果我们想一想计划总署预计1960年到1985年间人均年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4.7%,我们就会估计出法国经济学家甚至大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指望的真正革命。 为什么今天可以设想大大超出过去的经济增长率呢?在我看来,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依据如下:意识到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曾有利于改变企业主甚至人民群众对劳动和生产力的态度。昨天,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一系列个人行为直接瞄准的目标,有时候几乎对此察觉不到,今天,要达到什么结果,成为人们有意追求的目的,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来说都如此。 西欧大陆国家传播现代生产模式,经济中的某些产业如农业过去曾经抵制科技革命。在这些国家面前有较先进国家的例子,至少能够大概预测几年期限内主要产品的总量。为保证技术进步,人们耗费巨额资金进行研究,技术进步的速度确切地说加快了,而不是放慢了。总之,十五年以来,西欧国家成功地做到了大大减少周期性波动。这种波动只是表现为加速增长和缓慢增长的交替,而非扩展和收缩的交替。这些论点丝毫不打算证明大陆欧洲的经济,特别是法国的经济能够指望4.5%到5%的人均年生产增长率。这样的比率是例外情况,虽然过去已经出现过(1922年到1929年间的法国,1872年到1880年间甚至1871年到1889年间的美国)。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增长率在几十年期间保持不变,还是属于例外。再说它们不可能在一个世纪内保持在4%或5%。5%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11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130倍以上。4%的增长率导致五十年间增加7倍以上,一百年间增加50倍以上。 另外,不仅目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而且目前能源和原料消耗量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增长。我们计算了世界能源需求目前相当于50亿吨煤,到1975年将是90亿吨。按年增长5%算,石油的消耗到2000年将达到75亿吨。 从长远前景看,不存在能源和原料匮乏的问题,或者相反情况,不存在由于科学进步出现能源和原料富足的问题。我们要指出的仅是,生产的发展如同国家财政部门所估计,从此西方经济持续增长,今天欧洲的增长率高于过去按长时期计算的增长率,美国因其长时期增长率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总之,2%的增长率在一个世纪之后可使产值增加7倍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苏联的数字和斯大林去世以来十年的情况。苏联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在1953年到1958年间继续加速,自1958年以来速度明显慢下来。 在1953年到1958年间,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进行了多种改革,规模最大的是取消“拖拉机站”,所有改革都旨在使集体农庄庄员有更多的可能发展生产和上交产品。自1950—1952年至1957—1959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为6%。从那时开始,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这迫使政府于1962年1月1日宣布提高食品价格)。最近这些年农业的失败看来首先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开垦亚洲的处女地和其他一些决定从技术上说都不令人满意)。 最近几年的失败没有抹去斯大林刚去世后那些年获得的发展。与1958年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相比,1953年初至1962年初期间,牛的存栏数增加45%,羊的存栏数增加31%,增长速度是巨大的。人均肉类产品41.5公斤,相当于美国的40%左右。相反,两个国家的人均黄油数量应该说可以比拟,苏联1962年人均牛奶291公斤,比美国稍低(约低15%)。相反,如果我们把当前苏联农业的人均收入同1928年进行比较,我们会感到集体化的灾难性后果只是刚刚在消除。还不应该忘记农业收益是在全部劳动力缩减比例近一半的条件下获得的。 至于生活水平,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五年期间发展得很迅速。在1952年到1960年间,生活水平大概提高了将近50%(但起点很低)。1962年由于农业价格的上升和农业生产的停滞状态,生活水平下降了。根据西方的所有统计,苏联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水平,更不必说美国的水平了。 工业发展的速度在最近几年明显减慢,但还是属于快速的。1956年的计划于1957年9月被放弃。代之以七年计划(1959—1965)的出台。但事实上,这最后一个计划也处于半放弃状态,或者至少在农业生产方面和在实际生活水平方面它将不可能得到实现。甚至重工业都比预计的稍稍落后。 不管怎样,国民产值的增长率仍然很高。虽然估算各不一样,但最近十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大概在6%—7%。如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这个结果的取得是由于非农职位的大量增加(每年4%—5%),以及净投资的百分比非常高(根据A.伯格森教授的估计,在30%上下)。继承者们肯定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改革,力求使制度“合理化”。但是在最近三年内,回归到越来越集中的倾向取代了原来的分散倾向。虽然苏联的经济学家和领导人承认工业经济的复杂性和投资中的必要选择所提出的新问题,专断而精细的计划经济特点在农业和工业中都没有被消除,甚至没有明显减弱。在总产量,也许在技术质量方面(至少在某些领域),显露出与西方经济的靠拢。今天两种经济制度——诸如收入分配、价格作用、增长因素方面——几乎还是和十年前一样相去甚远。 越来越需要经理或技术专家的苏联仍然由党内人士在统治。官方思想体系继续证明党和国家的正确性。斯大林主义泛滥的反常现象已经消失。极端的恐怖形式已成往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化是不容置疑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被人们视为独一无二的普遍真理,并且不承认其他学说的存在权利。赫鲁晓夫先生接受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但是不接受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和平共处。 当然,形势不再像过去那样凝固不变。苏联领导人谴责个人崇拜,并不断重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有权拥有某些创作自由,但条件是忠实地遵循党的方针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天平的指针时而倾斜到自由主义一边——关于集中营的报道被发表——,时而倾斜到另一边,赫鲁晓夫先生提醒人们抽象画和十二音体系音乐是西方腐朽艺术,意识形态排斥和平共处。 换个说法,苏联式制度的固有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知识分子有完全的辩论自由,他们将会对根本信条、党和无产阶级的混同、国家正统性、党内人士的至高无上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拒绝给知识分子自由不再可能也不再应该被推进到斯大林式的荒唐地步。知识分子的自由与思想统治的稳定性究竟可相容到什么程度?苏联领导人在摸索中寻找答案,与西方和解以及与中国争吵使他们越来越急迫地要解决这个问题。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