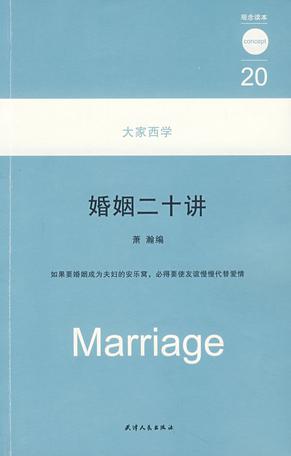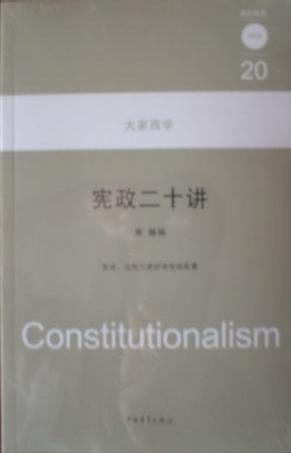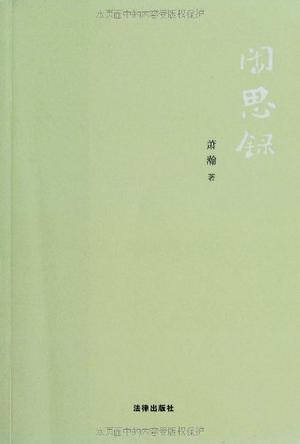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萧瀚
-
婚姻二十讲
编者序 历史中的婚姻及其未来 第一讲 爱欲、婚姻与城邦 第二讲 婚姻的智慧 第三讲 论爱欲 第四讲 论婚姻 第五讲 论婚姻与情欲 第六讲 乌托邦里的婚姻 第七讲 论结婚与独身 第八讲 婚姻的权利 第九讲 论婚姻、家庭与子女 第十讲 家庭的悲剧 第十一讲 孩子和结婚 第十二讲 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 第十三讲 娜拉与海尔茂的最后谈话 第十四讲 现代婚姻特色 第十五讲 婚姻美满及一夫一妻制的标准 第十六讲 忠贞不渝的爱 第十七讲 一夫一妻制与一夫多妻制 第十八讲 论婚姻 第十九讲 现代婚姻与智慧 第二十讲 传统婚姻中的夫唱妇随与御夫术 -
宪政二十讲
此文是去年写就的拙编《宪政二十讲》的序,此书现已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这篇序在出版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全文发表,现将原文发表于此。 2008年6月5日 宪政:人类政治实践的自然选择 萧瀚 性、财富还有权力,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三大动力。人分男女,所以性是第一动力,几乎不辨自明;财富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于是,在资源有限欲望无限的人类生活史上,财富也就极端重要;权力,则是秩序的需要,两人以上的人类生活,就需要划定自由与资源配置的界限,于是,权力就变得至关重要。 宪政就是关于权力有效配置的制度与学说。 从人类生存的历史来看,关于权力的制度远远重要于关于它的学说,但是学说并非无用,它常常具有协助制度良性化和传播性的功能,它与制度既能够形成良性互动,也会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它的发展史也就变得重要,编选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探讨哪些学说与迄今为止的权力配置制度之间关系密切。 无论是古典时代还是现当代,人类一直在为权力的有效配置烦恼,它直接涉及资源配置能否合理,关涉人类能否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如顾准先生所言,没有终极目标,只有永远的问题,因此,对宪政的研究也一样。目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宪政制度,依然存在新的创造点,关键恰恰在于各国自己的特殊情况,但无论如何,有效配置权力的原理则具有一定的共性。这正是我们要尊重历史、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因。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发现权力中的不同类型,于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无论哪种政体,政府的基本权力构成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行政权是执行规则的权力,而司法权则是对规则是否被有效执行作出裁判的权力,秩序就是因这三大权力结合行使而发生,如果这三项权力的配置是有效的,那么秩序就是良性的,反之,就是恶性的。 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开启的这一权力分析的经典传统,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虽然制度性的零星回应或者偶然自发回应一直没有停歇过,但理论的深度自觉回应并没有能够同步展开(虽有西塞罗、波利比乌斯等人的研究,但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掌握权力者都有无限追求权力的本能,一旦制度不能跟上,掌握权力者就挣脱绳索奴役他人,他们也就不能允许人们自由地探讨如何限制权力。若以私德而论,凯撒常被认为几乎完美无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必须能够自觉地知道应该限制权力,那么凯撒就不能算是一个伟大政治家,反而是刺杀他的勃鲁托斯更有远见:“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莎剧《裘力斯.凯撒》)。罗马帝制的建立在西方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原因就在于它开启了西方1500年的权力配置的畸形时代,也正是它使得善妒、不宽容的基督教主宰了世俗的权力。虽然基督教的超验正义在中世纪以暗光烛照着宪政主义的萌芽,但从总体上说,至少教会是负面的,教义所表达的正面效用,就像所有毒品对医疗可能都存在价值,我们不能说教会不是基督教的产物。宪政学家弗里德里希对此作出了重要阐释(但是本书限于篇幅没有收录)。 就在文艺复兴的曙光照耀欧洲的前夕,1215年,在英国,约翰王与教会和贵族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战争以约翰王失败告终,于是贵族和教会胁迫约翰王签署了一项协议——大宪章,旨在限制国王的权力,保证贵族和教会的特权,由于它对国王的权力限制性质,而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滥觞。 这一重要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轨辙,从此英国成为全世界宪政制度实践重要的启明星,他们的制度也成为宪政理论们最重要的灵感源泉。麦基文对英国中世纪的宪政实践所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历史,当时英国一批法学家如布拉克顿对罗马法的全面继承和创造,使得英国能够有效地逃离欧陆的天主教会专制,而实践自己的宪政制度,麦基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说:“中世纪宪法之区别于现代,因其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治理权和审判权的分离,二是管理命令和权利决断之法律效力上的差异。” 这些政治实践都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产生深远影响,洛克提出权力二分论便是基于此历史事实。之后,孟德斯鸠提出了权力三分说,不仅仅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起点上,而是进一步推进了宪政学说。他说:“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显要人物、贵族和平民组成的同样的机构行使以上所说的三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后果则不堪设想。”这一睿智而石破天惊的论断,开启了现代宪政制度的最重要理论,就是权力抗衡学说(这一理论从滥觞到成熟,有英国宪政学家维尔的全面梳理,他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关于均衡政制理论的历史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孟德斯鸠的地位,也有助于对现代宪政制度的核心价值——权力抗衡学说有更为透彻的理解,参见本书第十六讲),这是孟德斯鸠被认为现代宪政理论鼻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亚里士多德尚未探讨及这个问题。 随后,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对代议制政府许多具体权力运作的细节,作了清澈并且极富创造性的论说,他对言论自由的关注,对两院制是否必需问题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宪政理论,后来的杰斐逊甚至说:“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见言论自由的重要,这在后发而非自然演化的宪政国家尤其重要,并且已经被证明是无可撼动的历史性经验。一定意义上,密尔最初确立了宪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就是言论自由,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新闻自由是三权之外第四大权力之说,正是奠基于此。 财产权的重要性在所有宪政理论家那里都是极为重要的宪政基础,因此对它的论述大同小异,几乎所有的经典理论家们都对此有研究和论断,本书所选的当代英国宪法学家奥格斯借美国宪法对财产权在宪政制度中的重要性论述,言简意赅,值得一读。 至此,宪政的两大基石就是私有产权和言论自由。这充分说明权力相互抗衡而致权力配置有效,必须奠基于一个更为基础的抗衡,就是权利和权力的抗衡,这种抗衡在良性状态下,可以达到两者的均衡。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新大陆沿着英格兰道路,产生了一个现代宪政制度的模板——美国宪政,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设计的宪政制度,旨在达到人民的幸福。美国联邦宪法的出发点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得政府能够为人民谋取利益而不是压迫人民。因此,美国联邦宪法至今还是现代宪政理论和制度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美国人民接受联邦宪法的过程中,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写了85篇短小精悍、分析深刻、思想活泼、灵感勃发的文章,就是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成为现代宪政理论中关于权力抗衡理论方面最经典的作品。 宪政美国正是在一批杰出的法律家手里诞生,这充分说明了思想对历史的巨大塑造作用,思想巨人哈耶克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特别关注这群法律家在一个动荡而风云变幻的年代,是怎样将一块幅员辽阔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引向一条幸福之路。 在美国立国之初,国父华盛顿坚持不作国王,这是因为他看到英国政制的弊病,他的选择因其远见而正确,虽然我们并不能推断在美国确立君主制是不是会导致国王专制,但是华盛顿彻底地根绝了这一可能性,这正是他和凯撒的重要区别——即使相对于凯撒开启的共和政体崩溃来说,华盛顿的决定是历史的后见之明,但也是十分伟大的创举。 孟德斯鸠说英国是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制,但这件外衣并不是可以随便脱掉的,对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英国来说,国王的权力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议会消化,但它依然存在着对权力均衡的威胁,只是在英国政制下,它被不断地限制,从而产生了一些其他君主制所没有的良性效果,英国宪政学家白哲特对此的研究令人信服,然而,这在其他国家却往往难以复制。 正如美国是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先驱,英国作为老牌宪政国家、宪政之母国,他们的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常常产生新的杰出思想。当民主浪潮刚刚开始席卷全球的时候,上个世纪初的宪政学家詹宁斯因此而注意到民主在宪政制度中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敏锐且反思性地注意到三权分立学说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分析,因此,它只是一个理论的假设,而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却远比这种分析复杂得多,他认为在现实政治权力的运作中,三权交织,刻意区分只是不得不然,由此他认为民主比分权更为重要,民主比分权对于宪政来讲更为本质,这正好回应了托克维尔在100年前对美国民主的关注。 由于现实政治运作的千差万别和复杂,自由、民主、宪政之类的词语常常被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对这些概念的梳理就显得极为重要,帮助人们清晰地了解它们,并且在根本性上达成罗尔斯所谓的重叠共识,这是理论和思想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萨托利对宪政词义从政治社会学和语言社会学的角度作出了精彩的分析;而美国宪法学家奥德舒克则通过各国宪政实践的比较,总结了33条宪政规则;《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宪法/宪政》条,则对各国宪政宪法的基本结构作了共性分析。弗里德里希则从对宪政最大的敌人——极权主义的研究中获得宪政最纯正的信念和宪政最重要的本质——保障人权——信仰自由是人权的核心权利。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这话同样适用人类悠久的宪政实践史,就在宪政理论黯淡的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共和国和荷兰共和国在宪政的具体实践中,都没有什么理论的来源,这是令人饶有兴趣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些基本的甚至可能被酷评为幼稚的宪政实践给思想家们带来灵感,马基雅维利对共和政体的垂青正是基于此,从他这里诞生的近现代国家理性观念和主权论都与当时威尼斯共和国的宪政实践分不开。 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看,现代宪政在本质上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密切相关。 如果回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远溯三代,近观晚清,西周封建制(与郡县制相对)与礼制、汉初无为之治、唐初三省六部制、宋代文官选拔制、清代满洲贵族与汉官相互制衡以及督抚制度等历代政治智慧中都蕴涵了宪政的部分要素,尽管不系统。古代中国并非毫无约束政府权力的公法,更不是一句“2000年专制”就可以盖棺论定的,史家钱穆说过,历史上相权就构成对皇权的制衡,因此权力抗衡在国史中可算有实无名的概念,至少不是“卓越千古,推倒一时”意义上的全新舶来。中国从1911年清朝崩溃、帝制覆灭开始,步履蹒跚地进入现代,进入以构建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的时代。 但是,相对于西方,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对皇权制约的因素,并不能推翻宪政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相对陌生这一基本事实。这导致了百年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波诡云谲。史家唐德刚先生将近代中国百年转型,视为二百年历史三峡中的湍流激荡时代,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尚未从历史三峡中走出来。 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良好的宪政都相似,邪恶的政治各各不同。”而实际上,良治和恶政,各自都是相似的,从结果意义上说,前者的差别是政治形式的差别,而后者的差别只是程度而已。 然而,各国宪政的相似性却在一些非宪政国家,常常导致是否实行宪政的争论。在这个时候,重要的就不是有必要实行宪政的研究,对于宪政论者而言,他们所要研究的只是,如何在坚持宪政主义的基础上,研究具体到某国的宪政如何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与相似性相应的相异性反而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当代中国固然非宪政时代,但已进入公法时代。所谓公法时代,举其大端,是要厘清公权力的权限,划清公民自由和权利、社会权利与公权力的边界,是要追求有限政府的规则化、法治化。 具体而言,由经过正当程序产生的良法调整全社会的底线关系,法律就是底线规则,因此一国良治需要权威的立法部门。按照经典的宪政理论,立法部门应当由代议代表组成,以代表社会各界立法,唯有如此才可能制定良法,然而以中国历史验证,此项未必就是良治社会的必要条件,可暂置不论。 行政部门需按照法律执法,这是所有法治国家通例,现在的中国也在走向这条道路,似乎无需多加论证。 司法权是一项静态和被动的权力,司法权对于启动司法程序状态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具有更改甚至否定其权力之效能,因此其权威性举足轻重。如果司宪权归属于法院,那么司法权在整个国家的良治秩序中,具有最高地位。 社会权利是一种团体性权利,它是公民权与公权力之间的缓冲地带,所有良治社会都证明了正常行使社会权利对社会的公正与稳定具有巨大作用。它在协调公民与国家、社群与国家、社群与公民的关系中都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尤其重要。 公民权是每个个体公民所享有的各类基本自由和权利,于国家良治而言,公民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实现当为重中之重。 当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社会权利和公民权不健全,尤其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无法全面实现所导致的良治滞后甚至良治不能现象;二是司法权软弱无力,尤其司宪权缺席导致的立法错误无法纠正、行政专横难以遏制的问题;三是社会与公民缺乏公益诉权所导致的公共利益空亡问题,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公正与社会效率。 上述是横向的权力与权利配置,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涉及纵向权力配置的问题。 顾亭林先生曾有《郡县论》九篇,谈及中国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公权力配置上的痼疾,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未来中国必须制定出一套能够“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才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目前正在推行的省管县改革,似乎有亭林先生上述说法的苗头,但恐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改革的最高水平也只是回归到汉代的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模式上,无法达到目前世界上联邦制国家的纵向分权水平,因为除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分配问题,在权力最核心要素上的自治还是统治问题尚未明确。 横向分权与纵向分权必须综合解决,在解决横向分权时也必须同时考虑纵向分权的合理方案,反之亦然。如此才能使得公民权利、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各项社会需求能够同时处于均衡之中。 若以权力与权利的均衡配置为目标,那么三权分立还是N权分立(例如根据目前中国现状,如果让环保权独立,直接对人大负责未必就是坏事),人大至上还是法院至上(这要看司宪权归属于谁),精英立法配以人民监督的立法诉讼还是代议立法,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轮流,两院制还是独院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抑或半单一半联邦制(看需要看可能性)……这一切统统不能作为意识形态问题考虑,都不是讨论的关键——正如讨论姓资姓社意义不大一样。 理性的中国在权力与权利的配置问题上应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创造一种制度,以达到两者的均衡,为当代后世造福。关键只在于,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参诸外法,如果合乎中国国情,照抄国外的现成制度亦不妨,或根据需要损益其现有制度以补我缺,或者完全另起炉灶,都可以。 百年中国,吃意识形态的亏太大,现在我们应当放弃所有以僵化意识形态为鹄底的思维方式,历史与现实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出一幅图景,即中国未来的良治制度模式可能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 但愿这本小书中选编的经典作品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宪政事业有所助益,虽然这小小的20多万字篇幅,并不能将许多重要作品一一网罗,但是入选的这些经典作家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本身——而不仅仅是他们的结论,或许对我们有更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2007年8月12日于追远堂 -
闲思录
《闲思录》主要内容简介:写的过程,很随意也很惬意,有了电光石火的灵感,就写几句,凑足了20条,便发到我的博客新浪“追遠堂”。不想,许多朋友还挺喜欢。其中原因,无非是这些思絮很平常,没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嫌,写的时候很放松。 -
法槌十七声
有几篇文章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正义的召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行动》发在2001年8月号的《开放时代》上,此文部分内容在《比较法研究》发表过,因为网络误传的此文草稿在河北《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过(丁东先生在根本不认识我甚至根本找不到我的情况下无私地推荐了本文,在此向丁东先生谨致诚挚的谢意),《多数人暴政的警钟》(现合并在《耶稣之死与“群众性”司法》一文中)发表在2001年10月号的《读书》上(在此感谢盛洪先生的推荐),《底线伦理和罪恶职责》发表在2001年10月号的《开放时代》,《什么是真正的临终关怀?》发在2001年11月号的《开放时代》,《从马拉之死看政治谋杀》发表在2002年3月份的河北《社会科学论坛》。在此,我要感谢这些杂志对拙作的厚爱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尤其是时任《开放时代》杂志执行主编的李杨女士,对拙作的喜欢令我十分感激,并深受鼓舞。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