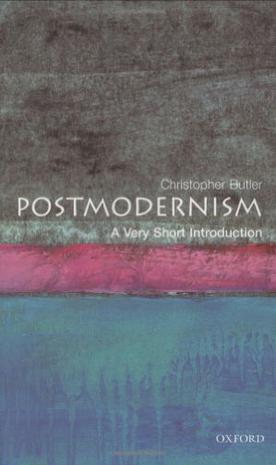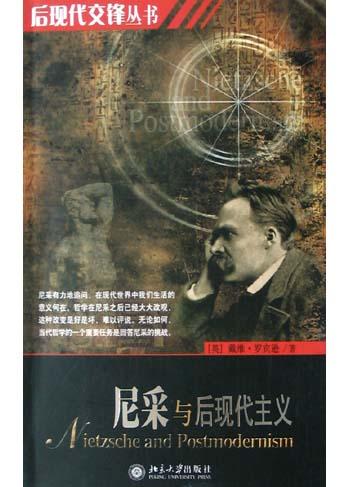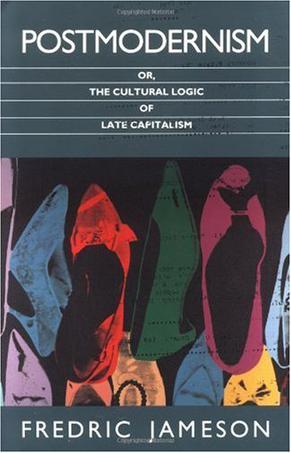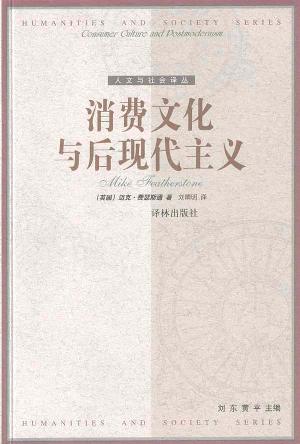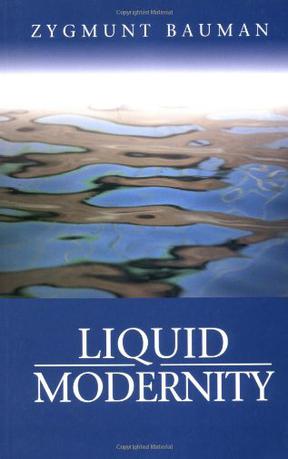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postmodernism
-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ism has been a buzzword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for the last decade. But how can it be defined? In this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Christopher Butler challenges and explores the key ideas of postmodernists, and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ory, literature, the visual arts, film, architecture, and music. He treats artists, intellectuals, critics, and social scientists 'as if they were all members of a loosely constituted and quarrelsome political party' - a party which includes such members as Cindy Sherman, Salman Rushdie, Jacques Derrida, Walter Abish, and Richard Rorty - creating a vastly entertaining framework in which to unravel the mysteries o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from the politicizing of museum culture to the cult of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
尼采与后现代主义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对20世纪的哲学和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看来还会继续到21世纪。尼采质疑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意义所在。他是一位对人类知识的可靠性和限度提出了很多保留意见的反哲学家。他的激进的怀疑主义扰动了我们所秉持的最深厚的信仰和价值。出于这些理由,尼采对我们现在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和哲学现象投下了深远的阴影。 《尼采与后现代主义》解释了这位反基督的哲学家的关键思想,继而对在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尔和罗蒂等思想家那里体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的中心论题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并最终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否可以合理地将尼采称为第一位伟大的后现代主义者。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ost-Contemporary Interventions Series)
Now in paperback, Fredric Jameson's most wide-ranging work seeks to crystalize a definition of "postmodernism." Jameson's inquiry looks at the postmodern across a wide landscape, from "high" art to "low," from market ideology to architecture, from painting to "punk" film, from video art to literature. -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简介: 所有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受益。 ——齐格蒙·鲍曼 前 言 我最早对消费文化发生兴趣是在七十年代后期。那时,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批判理论的倡导者们,在《泰勒斯》(Telos)与《新德意志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许多精彩论述与评论,激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有关文化工业、异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的工具理性化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和文化变迁过程。在我对老龄化这个(至少从社会与文化理论家的眼光来看)长期以来尚未被提高到理论化高度的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对问题的概念化形式给予了我特别大的帮助。尽管就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交错、代际经验、身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老龄化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人们很少联系到文化变迁的实质过程来探讨它们。批判理论家及其他人的研究(尤其是埃文((有关本书的英文人名,请参见《附录:中英文人名翻译对照》,下同。——译注)),1976),注重媒体、广告、影像及好莱坞模式等的重要作用,为弥合这一缺陷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并且进而提出了它们何以能够影响人们身份地位的形成和日常生活的实践等问题。此时我正在与迈克·赫普沃斯合写一本书,在该书中,我们将中年重新定义为“中青年”中更为活跃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对新市场的发育,对那种特别关注“中青年”如何能够保持年轻、健美的消费文化生活方式的蔓延,作出了看起来是更合理的解释。这个观点在一九八一年提交英国社会学学会的一篇题为《老年与不平等:消费文化与中年的重新定义》的文章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费瑟斯通与赫普沃斯,1982)。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个更为理论化的小文章《消费文化中的身体》(费瑟斯通,1982),后来,一九八三年,《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就消费文化问题特别出了专刊。 今天,尽管人们对“消费文化”一词的兴趣和对它的使用与日俱增,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及其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却不再被看成是很有意义的了。他们的方法取向,是通过对今天看来已经站不住脚的关于真实个体与虚假个体、正确需求与错误需求的区分,对大众文化进行精英主义式的批评。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瞧不起下里巴人式的大众文化,并对大众阶级乐趣中的直率与真诚缺乏同情。而对后一点的强烈赞同正是人们转向后现代主义的关键。然而,尽管在分析消费文化时,出现了大众主义((Populist,与民粹主义是一个词,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在中文里专指一八六○至一八七○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而本书中Populist、Populism则指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非精英/反精英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有很大不同,故译作大众主义,以与大众文化对应。——译注))的转向,但批判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诸如“如何区分文化的价值?”“如何进行审美判断?”以及与实践问题相关的“我们应该怎样活着?”等等,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被取消,而仅仅是被搁置到一边罢了。 这里,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它在后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章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相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参考框架和评论视角?如果在对消费以及诸如消费文化之类的概念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得以使自己的研究方式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主流当中,那么这又意味什么?消费与文化,这在过去一直都只是一种附带性的研究题目,直到最近还仍然被认为是派生的、边缘性的、女性化的,是生产和经济这些更男性化的中心领域的对立物,现在它们是怎样在对社会联系与文化表征的分析中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难道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与消费两者都在社会组织内或社会间组织中起着更为关键作用的新阶段了吗?贝尔、鲍德里亚以及詹明信是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关于我们已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或消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或后工业抑或信息社会的、“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抑或后现代性阶段的理论假设,确实具有新颖独特的色彩,它们足以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概念去关注问题。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与马克斯·韦伯的警句正相吻合: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这些观念在文化人(艺术家、知识分子、学者、媒介人)中的概念形成和消解过程。这使我们注意到发生在专家们的文化场域及各子域中的某些特殊的过程:已确立优势地位的主导者与外围者(Established andOutsiders )之间为争夺垄断并巩固符号等级秩序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只有从严格的文化模型、阐释、概念性工具、理论的意义上,去试图阐明那些影响着专家们的文化生产的过程,即文化专家们不断变化着的实践、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平衡关系,才能更好地阐释我们关于“外边那个文化”(cultureout there)的认知和评价。这样一个难题,即专家们各式各样并且捉摸不定的文化的专门模式和意指体系,与构筑我们每日每时活生生的文化结构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不仅对于理解人们为何转向对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文化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就我自己而言,对后现代主义的兴趣是我在试图理解消费文化时,碰到了许多难题后激发出来的,也是我去探索由贝尔、詹明信、鲍德里亚、鲍曼及其他人所提出的关于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直接关系而引发出来的。 所以,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我也流露出了对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问题的关注。在这些章节中,我不仅尝试着把后现代当作由艺术家、知识分子、或其它文化专家所发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来研究,而且还去探究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如何与可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及实践中广义的文化变迁相联系的。不应仅仅把文化专家们看作是在某种简单关系中,被动地充当着对文化变迁的标志和轨迹的特殊而修养有素的接受者、说明者、阐释者。他们在教育和培养观众((“观众”,原文是audience,英文中有观众、听众、读者等意思。原著中,多数情况下,audience都均包含了这三个涵义,是指文化产品的接受对象。为叙述简便起见,本书中文的翻译以“观众”一词来代表其余两层涵义。 ——译注))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动角色和兴趣,也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这些观众也凭借后现代这一称谓而对如何理解一系列独特的体验与文化产品变得敏锐起来。这也表明,文化专家与其它经济的、政治的、管理的及文化媒介的专家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及权力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他们对知识、文化导向手段和文化产品的垄断与反垄断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去问“什么是后现代?”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还要问:我们为什么、怎样才能对待这个特殊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否有人把实际的文化变迁与社会过程当作超越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证据,我们都需要去探求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所以可能的那些条件。 从高度抽象的层次上说,虽然根据一系列具体的特征,将西方社会历史中某一特殊的大断裂时期定义为“现代性”,并假定我们现在已经离开此“现代性”的核心而走向了别处,似乎是十分合理的。但是,这样定义本身就很成问题。这里的危险性在于,我们越是考虑那些当初被认作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反特征,它们就越是捉弄人似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似乎正在不断地变为现实。以前那些迷恋秩序、合作和系统性整体等观念的人,现在学会了去运用那种强调无序、模糊与差异的新认识框架来看待问题。然而,这并不是向“后现代性”迈出的一大步:后现代这个词,包含重大时代转变之意,它的可信性是从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样同样具有思辨色彩的术语中推演出来的。一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性理论,本身无所谓错误,除非它想试图借助超越经验研究(或者证明自己并不需要经验研究)来显示自己的可靠性,并使自己由此而取得合法性。遗憾的是,“后现代”及其相关语族中的词语常常就处于这种情况。的确,有些人就认为,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我们必须设法贬斥和废弃旧式的方法论,而不是去研究后现代,确切说,他们要我们去实践后现代主义,并建构出后现代的社会学。 这样,本书的中心目的就是去试图阐明后现代主义是如何兴起的,又如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富有影响的文化意象的。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并非仅仅是失去了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权力潜能得以实现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人为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知识和文化的生产、传递、传播等各个方面。本书各章还将认真探索被标识为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体验和实践,并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与这一范畴相关的各种更加宽泛的社会现象。然而,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些实际的体验和实践的时候,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在所谓后现代、现代性、甚至前现代的体验、实践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废弃那些诸如“传统”、“现代”、“后现代”之类的简单的二分法或三分法,而去关注那些最好被称为“跨现代”(transmodern,它的相关范畴是“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的体验与实践中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主题,这样一些理解当代社会中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作用的扩张所必需的概念及定义方面的问题,使得后现代变得如此饶有兴味。 这样一些关于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些理论表明,过去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直接从社会的角度以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去分析文化的,但是现在,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需要从基本意义上作一次大的修正。的确,很难把后现代问题与对文化进行理论概括的兴趣分离开来,因为正是这种引人瞩目的兴趣,才把后现代问题从一个边缘地位推向了各种学术领域的中心。这也反映在我们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的许多特刊时,对后现代主义所寄予的关注。哈贝马斯与福科之间的争论,是使我最早留心这个问题的契机,它促使我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编辑了“现代性之命运”的特刊(1985,2)。对这期特刊的准备及后来的连续反响,很清楚地表明,后现代主义问题需要从更广和更全的意义上去对待。这促使《理论、文化与社会》后来出版了“后现代主义”这本合期特刊(1988,5[2-3])。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对后现代主义是否仅仅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尚或者仅仅是某种短暂的流行术语,还存在着大量的怀疑。现在,很清楚,后现代主义比时尚更有生命力,并且也看得出来,它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其强劲的文化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及其他人对后现代主义如此感兴趣的原因所在。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个能够被整合到现有概念体系中去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科学概念,抑或更有甚于此,正出现(或正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式和认知框架,尚需拭目以待。诚然,对于那激发出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难题的后现代的出现,我们只能以双臂相迎。 我要感谢在《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中的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对我编辑此书的帮助和鼓励。我尤为感激与我详尽地讨论过许多观点的迈克·赫普沃斯,罗兰德·罗伯逊和布莱恩·S.特纳。我还要感谢斯蒂芬·巴尔、齐格蒙特·鲍曼、斯蒂夫·贝斯特、约瑟夫·布莱切尔、罗伊·博伊恩、大卫·钱雷、诺尔曼·邓金及罗伯特·埃利亚斯、乔那森·弗雷德曼、汉斯·哈菲坎普、道格·科尔纳、理查德·克尔明斯特、阿瑟·科洛克尔、斯科特·那希、汉·莫马斯、斯蒂芬·曼内尔、卡罗·蒙嘎切尼、乔治·斯道斯、弗雷德里希·泰恩布鲁克、威廉·凡·雷詹、安迪·韦尼克、克斯·乌泰斯及德雷克·威尼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与他们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许多研究主题。此外,我还要提及在提塞理工学院(TeessidePolytechnic)社会研究与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的慷慨支持,特别是劳伦斯·塔斯克和奥利佛·科尔撒德对我在编辑《理论、文化与社会》这个独立期刊方面所提供的组织支持与鼓励,它在我增进和保持对后现代问题的兴趣方面是至关重要的。我还要感谢詹·康奈尔、马丁尼·梅尔伯和数据室对本书各章节的许多修改的细致耐心的打字输入。 本书各章节的原出处是: 1. 《现代与后现代:定义与阐释》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在伦敦大学哥德斯密斯学院、一九八八年三月在特里特大学比特波罗分校的讨论课上宣读过,一九八八年五月在意大利阿马尔菲的阿马尔菲欧洲社会学奖大会上亦作过宣讲。一九八九年六月,此文修改后,在里斯本的社会学研究与调查中心曾作过演说。当时的题目是:“对后现代的追求”,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1988年5[2-3])。 2. 《消费文化理论》是一九九○年发表于《社会学》(24)上的一篇论文《消费文化的视角》的修订稿。 3. 《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学》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利兹大学的理论课上及一九八七年六月在不来梅的“关于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欧洲社会学理论团体会议”上作过演讲,并先后以英文、德文等文字分别于一九八九与一九九○年被收入H.哈菲坎普主编的《社会结构与文化》(Berlin:de Gruyter)。 4. 《文化变迁与社会实践》曾于一九八七年五月,由国际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格·科尔纳在堪萨斯的劳伦斯组织的对弗雷德里克·詹明信著作的研讨会上宣读过。修改后发表于D.科尔纳主编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批评》一书中(华盛顿:Maisonneuve出版社,1989)。 5.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最初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新奥尔良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的讲演,同年九月在哥本哈根的“作为历史的现代性大会”上及同年十月在瑞典伦德大学(LundUniversity)的讨论班上也作了相同演讲。此文被收入S.那希及J.弗里德曼主编的《现代性与认同》一书(牛津:Basil Blackwell)。 6.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最早是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为在提尔伯格大学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大会”上的提交的论文,后来被收录在恩斯特·梅吉尔主编的《日常生活:闲暇与文化》(Tilbury,1987)并于一九八七年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1987,4)。 7.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是为一九八九年六月在罗特德曼的“第七届欧洲闲暇与娱乐协会关于未来城市的代表大会”提交的演说论文,发表于会后由L.J.Meiresonne主编的论文集《未来的城市》(TheHague: Stichting Recreatic,1989)。 8. 《消费文化与全球失序》是一九八七年于西印度群岛圣·马丁举行的“宗教及寻求全球秩序大会”上的演说论文,它被收入W.R.Garrett与R.Robertson主编的《宗教与全球秩序》一书(NewYork: Paragon House)。 9. 《共同文化抑或非共同文化》最早是为高等教育基金会一九八九年三月在牛津圣安娜大学的“高等教育价值会议”提出的论文,此文修改后发表于《高等教育反馈》杂志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四期。 -
Liquid Modernity
In this new book, Bauman examines how we have moved away from a 'heavy' and 'solid', hardware-focused modernity to a 'light' and 'liquid', software-based modernity. This passage, he argues, ha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 to all aspects of the human condition. The new remoteness and un-reachability of global systemic structure coupled with the unstructured and under-defined, fluid state of the immediate setting of life-politics and human togetherness, call for the rethinking of the concepts and cognitive frames used to narrate huma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ir joint history. This book is dedicated to this task. Bauman selects five of the basic concepts which have served to make sense of shared human life - emancipation, individuality, time/space, work and community - and traces their successive incarnations and changes of meaning. Liquid Modernity concludes the analysis undertaken in Bauman's two previous books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and In Search of Politics . Together these volumes form a brilliant analysis of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 by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thinkers writing today. -
现代性的后果
简介: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导读: 本书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社会形式的特殊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相当吸引人的视角。吉登斯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吸收了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社会思想传统,并且让不同的理论家们作为对手相互竞争,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不仅建立在整个传统之上,而且建立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之上。 ——赫伯特·林登伯格 结 语 最后,让我对这本书的论题作一个简要概述。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优越地位”:西方的统治。尽管现代性的组织者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去取代从前确立的教条,现代性还是有效地融入了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的知识,自身都是循环性的,尽管“循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前者,它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科学是纯粹的方法,所以“业已接受的知识”的所有基本形式原则上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社会科学假定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循环,它们对现代制度来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科学创造的所有知识,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并且,当它们循环性地往来于它们所描述的环境时,实际上它已经是“修正”过的知识了。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特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经常贴着后现代性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验,在那里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而且,从侧面来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天摄入的信息量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可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同时既是主体转变也是全球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书以此开篇的时间问题上。就最初提到的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基础的三个基本部分而论,一个后现代世界可能会像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那么它们也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作为结论,只须对此略加评论就够了。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短暂性二者,都是对立的。乌托邦的预期对事务的未来状态划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阻断了现代性的无穷无尽的开放特性。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像,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这种稳定性反过来提供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由于意识到社会的普遍性是受制于人类对它的控制力,这种安全感再度加强了。这将不会是一个“向外崩溃”并变成分散的组织的社会,但毫无疑问,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世界将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吗?似乎有这样的可能。然而,考虑到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切断乌托邦的沉思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本书这种类型的研究相比,它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