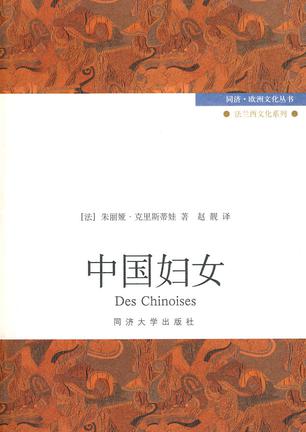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Julia_Kristeva
-
中国妇女
1974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该年5月,作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论坛《原样》(Tel Quel)的一员,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Bmlhes)、菲利普·索列尔(PhilippeSollers)以及《原样》杂志主编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等人对中国作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产生了大批的相关著述。克里斯蒂娃应法国妇女出版社之约,当年就发表了这本纪实游记。 在本书中,克里斯蒂娃对两千年来笼罩在中西方文明之间的神秘面纱作了某种原创性地揭晓。她凭借在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人文学科理论上的广博知识,抓住母性和性别差异的主题,以中国家庭为横坐标,以中国历史为纵坐标,从政治、宗教和文学等各个方面作出以点带面的全景式分析。全书理论性强,由于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使得本书较为艰涩难懂,本书的论述立场也曾受到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等女性主义作家的质疑,在有关殖民主义理论、身份和统一性等等问题的讨论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由于客观翔实的记录部分,对于促进中国妇女运动和女性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恐怖的力量
內容簡介:為何談論卑賤?為何存在一種既非主體亦非客體的「某個東西」;它不斷地重新現身,讓人臉色蒼白、令人作噁,又教人著迷。為何這些情緒因卑賤體而來? 它無關精神官能症。我們只能在恐懼症、在精神病中瞥見它的身影。這涉及一種佛洛依德曾經略微碰觸,卻又巧妙避開的爆發狀態。今日的精神分析,若想擺脫單純地老調重彈而走得更遠的話,則應益發迫切地豎耳傾聽。 因為,我們的歷史和社會正迫使我們這麼做。進入恐怖的核心。儀式、宗教、藝術,不都一心一意召喚著卑賤情境嗎? 神聖領域不僅關乎弒父禁忌,亦涉及亂倫禁忌:玷污儀式。聖經律法強烈暗示著食物中所包含的根本不潔性質。當基督信仰的罪愆概念將褻瀆憎惡感內化之後,又企圖使它在「道」(Verbe,神的話語)中消失。所有的象徵秩序都縈繞在這樣的隔離程序中。而我們所寓居的世界,正在引爆這個程序的危機。 這是文學之所以能為我們帶來奇特啟發的原因,比方杜斯妥也夫斯基、羅特雷亞蒙、普魯斯特、亞陶,還有,無疑展現著極度明顯症狀的謝琳。 現在,向我們走來的這位邊境的居留者,無固定身分、無固定慾望,亦無固定居所。它不斷流浪、誤入歧途,苦樂參半。在這齷齪人世,他無望地漫遊著。 這便是卑賤的主體。 作者簡介 茱莉亞.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法國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巴黎第七大學教授。一九四一年出生於保加利亞,二十五歲至法國。主要思想背景為康德.黑格爾之哲學傳統、語言學以及巴赫金的後形式主義,後轉向羅蘭.巴特的後形式主義,並開始研究佛洛伊德和拉康。一九七三年以《詩語言的革命》(La Revolution du langage poetique)於高等社會科學研究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正式成為精神分析師,同時也是巴黎大學的語言學教授。她以後結構主義理論,分析語言、社會、和個體及其心理與慾望之間的關係,持續書寫一系列具有影響力的文化批評著作,帶給許多知識領域新的啟發及深度,包括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和當代女性主義,甚至以其東歐出身的馬克思主義背景和個人才氣,回饋啟發給她最重要的老師,羅蘭.巴特。並在這三十年來,成為藝術人文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法國作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語言分析》(1969)、《詩語言的革命》(1974)、《恐怖的力量》(1980)、《愛的歷史—故事》(1983)、《黑色太陽》(1987)、《沒有國族主義的國族》(1990)、《我們之間的異鄉人》(1991)、《靈魂的新痼疾》(1993)、《精神分析的力量及界線I, II》(1996, 1997)以及近作《女性的天份I, II, III》(1999, 2000, 2002)。 目錄 中文版序/克莉斯蒂娃 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劉紀蕙 第一章 卑賤的取徑 第二章 害怕什麼 第三章 從污穢到玷污 第四章 聖經的憎惡符號學 第五章 ……除免世罪者 第六章 謝琳:非戲子亦非殉道者 第七章 苦痛/恐怖 第八章 這些女人糟蹋了我們永恆的生命… 第九章 「猶太地活著或死去」 第十章 太初與無盡 第十一章 恐怖的力量序 在我的著作中,《恐怖的力量》一書並非第一部以中文版出版的作品,但它的出版卻最令我欣悅。我十分感謝譯者、出版社,以及這份禮物未來的讀者。 令我向本書出版致敬的原因有許多。 首先,我對中文及中華文化的熟稔──我以曾在大學時期研讀中文自豪,同時卻深知面對此一浩瀚宇宙,這是何等不足──讓我得以衡量橫亙在西方、猶太-基督、印歐信仰內的神聖界,與中國傳統之內、本身即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聖領域之間的距離。您眼前的這本書,目的是在嘗試開啟一道傾聽我們這一方的宗教情感的頻道。 現在,由您來估量我們彼此的距離,聽診我們的殊異性,評斷在我們和您之間是否有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我並沒有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對話的夢想,這是樂觀的人道主義所歌詠的古老田園詩。然而,一種相互的敬意應是可能的吧?在西方,有一些人試圖如實地閱讀中國,避免濫用同化。而相對而言,在此西方紀元第三個千年之初,當西方世界以其過時的優越自負作遮掩,逐漸退卻為簇擁成人類花束的千百朵花中之一時,您有沒有可能對西方文化蘊生一種善意的、願意理解的距離?總之,在撰寫此書之時,推促我書寫的動機,是為了分析我們的文化傳統對於「神聖界」和「絕對性」所抱持的傲慢自負,進而從中閱讀出「權力」與「賤斥」:但其目的不在破解它們(焉能為之?),而是為了打開探問之道。 使我感激的第二個理由更有其現時意義。我猜想,細心的讀者將在字裡行間,發現有助於省思當前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連結的諸多線索;它們將幫助讀者看出宗教與恐怖主義之間無法避免的關聯;至少,此關聯在我們這個文化傳統中是無法避免的。在華盛頓和紐約受到攻擊之後不久,多少正直的美國、法國公民,以及涉案之自殺飛機攻擊者的鄰居和同窗,都聲稱難以置信一位父親、一個認真的大學生或一個平時溫馴的信徒,竟會是恐怖的殺手。而在其他狀況裡,serial killer(連續殺人犯)或戀童癖的鄰居和同窗,在事發後感到震驚的程度,亦不下於此。 在理性主義與實證主義盛行的年代,有許多人們習於將人類視為理性的動物,由唯一、表象的邏輯所支配。不得不宣佈棄權的理性,如此懊喪地歎道:「一個人怎麼可能成為恐怖份子?」由於心理分析的理論進展未能影響大眾政治文化,我們很難想像表象並非本質,而個人在精神病或心理倒錯的壓迫之下所展露的虛偽人格,掩藏著慾望的深淵;尋根究底,此慾望即為死亡慾望。我們對於經濟的悲慘處境如何能推促人走上自殺或屠殺之途的考量,不應妨礙我們重視人類行為的潛意識深度。現在應是我們重新審視進步主義妄想的時候了,此一重估將能引導我們致力於提昇研究者的心理觀察能力。我並不是在鼓吹質疑的心態,而是衷心地期待在對於他者的研究取徑中,能否少一些天真。比起曾經驅趕惡靈、直指地獄的宗教,我們其實要來得更加幼稚。拒絕宗教信仰,並不代表我們便能自動地抵達清醒、澄明的境界。我們還必需擁有從中辨識出那些最具體或最隱晦的變種的能力;幸有人類學和心理分析之助,我們才能將之逐出巢林。一段長遠的教學工作正等著我們。 此外,所有的宗教不僅從未低估情感的、複形的潛意識邏輯,並且善於挪為己用;暫且不論此挪用是好是壞。當我們發覺蘇聯共產主義中粗暴的無神論,到頭來除了以寬容主義為掩飾,接受先後由美國人、歐洲人所提倡的與宗教人同謀的態度,以取代意識型態,而毫無其他選擇可言,怎能不感到痛心?現今,有許多沉靜祥和的學者,透過令人尊敬的廣播電台麥克風,向我們傳遞著神學的注釋,而不作任何分析。唯恐煽動宗教衝突,人們自滿於吹噓某個宗教經集的文化優勢(這的確是事實),不但忘卻了其他充滿激情的對等物,其實是構成此一經集整體的一部份(這也是事實),更忽略了這些蘊涵多義性的經文,必定伴隨著眾多不同版本的詮釋;而正是當這些不同版本的詮釋,與情感和悲慘相遇時,始導至恐怖主義的出現。即使我們深知,在宗教及其整體主義之間存在著差異,這卻不妨礙我們平心靜氣地檢視那些容許跨越二者間隙的舷橋。原因是,當恐怖份子炸毀一架飛機的時候,在他腦際盤旋的並非莫札特的奏鳴曲,或莎士比亞劇本中的台詞,亦非畢卡索的畫,而是其宗教教條中的某幾節經文!杭亭頓(Huntington)在針對文化域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文化域可能導致宗教衝突;其研究分析往往被詮釋為,對於某一不可抗拒之命運的觀察結果。然而事實上,我們亦可將其解讀為,對於不同宗教傳統的邏輯進行深入理解的邀請,以便進一步分析其優越性,及其可能導致的絕境。我們不應將這些邏輯視作危機時期的想像解決方案;但不幸的是,不僅經濟的悲慘使它們已被升格為想像的解決方案,我們對後者的默認,亦增強此一趨勢。事實上,啟蒙時代在現代精神科學中,順利地找到了它的延伸,這使我們在面對狂熱主義時,並不如人們所說的那麼手足無措。我們不能假借寬容與多元文化主義之名,太快就忘卻啟蒙時代所留下的光明。 最後,我的思考路徑隨著對於謝琳(Celine)作品的閱讀,逐步進入另一個亦不脫現時意義的探問:文學究竟是恐怖主義的共謀,或是它的解藥?冒著引發讀者憤慨的危險,我認為在文學中存在著兩條道路,引導它與恐怖主義相鄰:一是文學深植在國族語言中的根脈,二是文學在其結構上即參與著恐怖的形成。 至少自浪漫主義作家開始,在這片任憑作家的想像和國族語言相逢的神聖境域上,即已滿是縱橫交錯的軌跡。 其中的一道,自奉為國家特性的崇拜儀式與捍衛者,而作家因著他的職業或志業,化身為與國族風格等同於國家崇拜的頌讚人。在這些作家當中,是謝琳以最坦蕩的語氣,洋洋陳述這個介於各種語言與各個人民之間的戰爭邏輯,文中充滿佯裝的愚蠢,卻極具感染力。他曾如此說道:「法語多麼高貴莊嚴,但四處卻充斥著那麼多該死的蹩腳語言。」 然而,為化解此一趨勢,無論如何、不可避免地以國族語言進行書寫的文學,早在時下的全球化運動、及移民作家所謂的「混種」文學出現之前,便已藉由無法共量的作家對社群俚語的滲透,超越了國族層次;這是因為,一旦獨特化到極致,風格不僅將在個人層次上、亦會在國族層次上形成去認同作用。我們還記得,馬拉美(Mallarme)曾欲寫出一種「外異於語言的、嶄新的、全面的文字」;而喬伊斯(Joyce)在《尤里西斯》和《芬尼根守靈夜》裡,則將語言根深蒂固的執著,推導至嘲諷當地人:喬伊斯,或許就代表著永遠不可能成為當地人。 想像界的複音性質,導致它的無認同性。而九一一事件及隨後的爆炸事件中的自殺狂熱分子,不論是就美學或政治層面而言,可謂毫無想像;他們將自身的驅力直接付諸行動-時或出自需要,以及可理解的殖民羞辱,但卻不因此而取得任何合法性。我深知這樣的見解在狂熱主義的粗暴之前,所可能喚起的激憤。然而,我還是必須說,想像文化有可能開展被任一派別的整體主義所僵化的社會關係領域,並且舒緩身分認同的蜷縮。閱讀、教授文學、揭示它的複音邏輯以對抗宗教的單一邏輯主義,不啻為一種政治治療。 即使如此,我並不認為虛構小說代表著一種絕對的護欄。因為,新語言的創造,雖孕育著一個嶄新的想像界,它卻是根植在創造的主體性所面臨的難以承受的危機之中。意即,在美學創造的過程中,作者置身於一個紊亂的心理區域,在那裡,他者尚未成為客體,原因是此時失落了身分認同的自我並非主體。在此情況下,他者乃是卑賤體(abjet),即一種卑賤形式,一個既引人反感、卻又令人著迷的極端;如同昔日的乳房、母親和父親 - 那是在「我」接受他既鎮壓、又護佑的至高律法之前。美學行動迎接世界的卑賤,有時甚至不惜使用類似的武器與之對抗:暴力、毀滅他者、毀滅自己,極盡諷刺、詆毀之能事,挑釁讀者、強暴公眾、甚至強暴表達工具本身,直到以自殺毀滅作品、殺害自己。 美學的判斷(審美的確是一種判斷),從來就不曾是二元性的,而今日較往昔尤不如此。藉著邀請我們重新認識人類行為中的所有面向,它展現了包含在此行為中的各個組成成分(布希或海珊;巴勒斯坦或以色列;受害者或劊子手)。然而,在它與恐怖之間永遠可能存在的共謀關係之外,藝術終歸是開放了邁向一個更複雜、更平衡、更公正的思考模式的機會;此處庇護所,使得在這個一昧追求高效能實現的文明社會中被迫害的思想,獲得了運轉的可能。而這思想庇護所、或這在所有行動之前形成質疑再現的能力的崩毀,豈不是包括政治恐怖主義在內的新型態靈魂疾病所具有的最大特徵? 反之,即使文學以其自身的方式,亦為恐怖的一種形式,但正因為它座落在再現和語言之內,便令它成為一種有助於思考恐怖自身之內在成因的恐怖形式。這效力有限、影響卻深遠的解藥,不可說是微不足道,可用以抵禦那不僅來自外在、亦從內裡對我們進行雙面襲擊的恐怖主義。 從今以後,不管願不願意,中華文化已是全球化世界的一部份;在此世界中起舞翩翩的,不僅是全球化經濟,亦包括我在此提到的種種問題。而您的文化傳統、您的獨特經驗,是否將改變、重複、或擴大這些問題?人類的未來,則取決於此一問題的答案。或許,《恐怖的力量》一書的翻譯和閱讀,將可成為這條道路上的一個階段。祝您好運!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