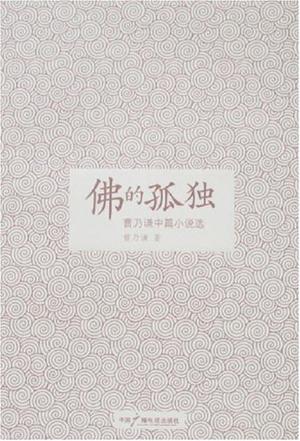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曹乃谦
-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是曹乃谦作品集中的一种,收入其中的是他主要的散文代表作。主要有《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扫院老汉武师傅》《我与瘫痪的一次零距离接触》《伺母日记》《儿子的忏悔》《回忆我的父亲》《哈罗,雷呜》《黑色的记忆》《快乐围棋》等。曹乃谦的散文写作除了感情真挚外,语言是他的最大特点,那种糅合山西雁北地区的方言,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
温家窑风景三地书
这部书稿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是马悦然、陈文芬和曹乃谦三人关于《温家窑风景》的来往信件(电子邮件),主要涉及翻译过程中的语词的技术问题交流问题,这些信件是独家首发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有助于理解曹乃谦的作品。第二是各家媒体对曹乃谦的采访,第三是曹乃谦的另外几篇散文。从内容看,这部书稿所收文章都与著者的创作有关,有散文、书信和访谈。这些内容使得读者对曹乃谦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进而更好地理解曹乃谦小说所包含的深刻意蕴。 -
佛的孤独
本书是曹乃谦的中篇小说选,包括《佛的孤独》、《山的后面还是山》、《冰凉的太阳石》、《陨歌》、《鱼翔浅底》五篇作品。作者通过这五篇作品,写出了一个出自孩童少年目光中的人性当中温暖深沉的爱。这些小说语言简白而家常,处处流露出作者记忆里面最初的那种从前说不出口的挚爱。穗儿、柳姐、善缘和尚……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可爱而令人留恋的。书中那纯洁的初爱唤起的是人们心中温暖的记忆…… -
最后的村庄
本书精选了曹乃谦19篇短篇小说作品,包括《野酸枣》、《沙蓬球》、《最后的村庄》、《斋斋苗》、《亲圪蛋》等。这些小说中,曹乃谦采用一贯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用自己的口语毫无遮拦地直抒胸臆。每篇小说都是来自那块贫瘠洪荒的土地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这里有活在不可思议的卑微中却被作者以其神性与创造力升华了的宛若“地母与女神”的痛苦的女性;也有猥琐、卑微、需索人性欲望的小人物……作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衷心地发出对生命的叹息以及对于“人”的温暖和爱眷。 -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
《你变成孤子我变成狼》主要内容: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又是将军在指军作战又是樵夫在山中砍柴又是巫汉在装神弄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又在天上翱翔又在地下奔跑又在水中击浪;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又在引颈高歌又在挥毫泼墨又在翩跹起舞。 -
到黑夜想你沒辦法
曹乃谦是山西的警察,也是作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赞美他:「我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 本书描写苦寒、封闭、吃面的雁北农村的生活,在那片赤贫与苦旱的农村大地,特别着重在对食慾和性欲这两项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欲望的描写。 文学家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就推荐曹乃谦,去世前还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湖南的何立伟、哈尔滨的王阿成、山西的曹乃谦和我的创作思想一致,走的是平实的路子。评论界称他们受我的影响,爲抒情现实主义和风俗画笔致。他们都正寂寞地写着。」 超越俚语的障碍,读者必能得到巨大而真实的感动。 -
曹乃谦小说集
“他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作家。……他的东西实在写得好!” ——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原载2000年10月12日台湾《联合报》 “曹乃谦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是在瑞典文学院图书馆订阅的《山西文学》上偶然读到了他的作品,当时我就立即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了英文。” ——2005年10月在北京“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悦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我们从曹乃谦对这样的荒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叙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喊叫: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实的叙述,而如实的叙述中抑制着悲痛。这种悲痛来自对这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的严重的关切。我想这是这一组作品的深层内涵,也是作品所以动人之处。 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是简练的,但是有时运用重复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子,这种重复、近似造成一种重叠的音律,增加了叙述的力度。 ——摘自汪曾祺先生为《温家窑风景》一书所写的代序 ■章节选录…部分内容预览 部落一年 一九七四年过完国庆节,我们矿区公安局的一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先说我二十四五正当年前程无量,后说我一贯要求进步并且表现突出,最后说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把一个重要任务交给我。那就是,让我去北山区的榆钱沟村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带队队长。时间是一年。他也没问我同意不同意,就说给你放三天假,回家准备准备。我说我虽然是个单身汉,没有儿女拖累,打起背包就能走,但我有个寡妇母亲。领导说那你也可以常回来看看。又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出来,组织帮你解决。我想了想说,能不能给我妈拉一车炭。领导说,没问题,你回家等着,三天之内就给你送去。敬爱的领导说话算话,第二日的下午就把一车炭给送来了,四吨多,够我妈四年烧。我很高兴。 十月二十日,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矿区区委派车把我送到了北山区,还说等腊月二十三再来接我和知青回来过年。北山区区委开了欢迎大会,还给我们吃了一顿。 拖拉机一路突突突地吼叫着,吭吭吭地咳嗽着,滑东擦西向前跌撞。 拖车上拉着我们十来个要到各村去上任的知青带队队长。像往地里送粪似的,每到一个点儿,我们这些人就被留下一个。最后剩下我自己。 驾驶室那高大的轮胎甩起的泥块泥片,直往车上溅。我喊司机慢点,可他仍不减速。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理睬我。在一个梁顶上,拖拉机停住了。司机跳下地,解开裤子哗哗哗尿了一阵,尔后猛烈地打了个冷战,看那样子很是舒服。尿完,他冲我转过身。就颠颤手中的那管黑物件就说,想坐坐驾驶室哇。 这种拖拉机本来是没有驾驶室的,他们给焊了一个,又在里面的左侧焊出个座儿。当时的公社没有小车,这种改造后的拖拉机就成了公社头头们的坐骑。有个贵客什么的重要人,也靠它来接送。 驾驶室里的噪音小多了,没有泥东西往里飞溅,也用不着两手紧扒车厢的帮子提防摔倒。安安稳稳的就好像是坐在北京吉普里。 司机四十多岁,是个壮汉。刚才在区委招待所吃饭时胡茬上粘着的一颗大米粒儿还在,胡茬黑黑的米粒白白的,很是显眼。我问说师傅您贵姓,他说球,接着又说杨。我问说您是区上的还是公社的,他说公社的。我又问了几句别的。问他家里几口人,几个孩子。他没回答。看他不待要搭理我,我也就不再问了。 从后窗看看拖车上的行李,上面溅满了泥。幸好我妈给包裹了一块厚塑料布,要不就糟了。 刚下过雨的云灰蒙蒙的。天底下没飞着燕子也没飞着雀儿,连只乌鸦也没有。庄稼都被割走了,田地一片片一块块,形状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像是些补丁补在坡梁上。 又爬上一个梁顶,杨司机说了声“到了”。可他仍没跟我说,在跟路说,要不就是自言自语。 前面二里远近的那处沟坡上,横着竖着一些窑。有几棵不知是什么树,拐拐弯弯长在那里。还能看出村北有处场面。场面上堆着的不知是什么庄稼的秸垛,在这里望去,像是几个扣着的破毡盔帽,又像是几堆突起的坟头。 眼前这景象实在是荒凉,可我的心还是不由的一阵阵地激动起来。 这就是榆钱沟。 这将是我要生活和工作一年的地方。 知青共八个人,五个女孩子三个男的。住的是排房。墙是一砖到底,可房顶没瓦,是土皮的,一丛丛枯黄的草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抖动。这是三年前上头拨专款给盖的。和社员的土坯窑比起来,知青们住的房该是宫殿了。排房前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像个操场。拖拉机就停在了这操场上。 大队刘书记和革委吴主任早已经在等着我。还有大小老少十多个人在排房前看红火,他们一个个都脏哄哄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有的上身穿着棉袄可却是光着脚板。他们活像一群要饭鬼。 吴主任吩咐一个女知青说,“告给黑豆家的,就说来了。”刘书记说,“用不着。砖头会说的。”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砖头,就是公社的那个杨司机。 收拾完洗了把脸,我跟着书记和主任到了黑豆家。人们称作砖头的那位杨司机早已经坐在了炕上,看样子他也洗涮过,黑胡茬儿上的那颗很好看的白米粒儿不在了。 炕头坐着个小老汉,有六十多岁。他欠起屁股喜盈盈地招呼我们说,“快上哇。您儿们快上炕哇。” 吃饭当中我发现,杨司机看外表是个粗人,可他对小老汉却老哥长老哥短的挺尊重。不像书记和主任,一直管小老汉叫老黑豆。 老黑豆也真是老了,夹菜老是夹不紧,老往炕上掉,掉下炕又用手捏起往嘴里送。后来他干脆把左手当成碟儿,就住筷子,这才不往炕上掉东西了,要掉就掉在手心里,再把手心捂在嘴上往肚里吸溜。 喝着酒,门帘一掀进来个女人问说上饭呀不着呢。刘书记给我介绍说,这是黑豆老婆。 “啊!”我差点儿给喊出声来。她刚进门时我以为是黑豆的女儿或者是别的来帮忙做饭的妇女干部。尽管煤油灯不亮,可我也能看得出这个女人是白白净净标标致致的。如果把发型改改,再穿上城里头时兴的服装,说她三十也保准有人信。她怎么竟是炕头上坐着的那个小老头的妻子?我觉得真不该是这样。人们常说鲜花插在牛粪上,看来真有这事。 我对酒没瘾,中午区上招待的饭菜又挺像个样子,再加上一路的颠簸我有点疲乏了。我说我想回去休息。杨司机好像盼我快点离开,他“仙云仙云”地喊过一个大姑娘,让她拿手电送我。 仙云差不多有二十岁,个头不高,眉脸倒是耐端。路上问过,知道她是老黑豆的大女儿。我想问问她妈多大,没问。 她拿手电给我照着路,上坡下坡时还用手托着我的腰。后来问我说你是公安咋没挎枪。噢,她刚才托我的腰感情是在摸我有没有枪。我说来这里的时候把枪上交了。她问我是“五一”的还是“五四”的。我说是“五四”的。她说她打过“五一”的没打过“五四”的。她问枪,使我想起她们家正面墙上贴着“射击能手”的奖状,那一定是她的了。一问,果然是。她说她真想当个兵,就是武装部没人。说着,到了知青排房。 我的宿舍没锁门。进了屋,她用手电给照着,点着煤油灯。知青们过来了。说笑当中我才知道仙云原来是村里的妇联主任,还兼着民兵副连长。真看不出,黑豆小老汉还有这么个了不起的女儿。 半夜,正睡得香,听见有人就奔跑就喊叫杀人。“杀人——”,“杀人——”。睡梦中我被这喊叫声惊醒,一跃身爬起来。可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在机关的值班室?在追捕逃犯途中的旅店?后来才想起这是在远离城市的榆钱沟。我披着从家带来的警服棉大衣出了院。喊叫声和奔跑声没有了。来的时候那浓厚的云已经散开,天上露出了星星,还有一丝月牙儿。我想我这一定是做了恶梦。骂了自己一声神经病,就又返回屋睡了。 第二日早晨,有人在宿舍门外轻声地叫曹队长。 我们这批带队队长不仅要管好知青,还要帮助大队进一步深入地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还让我们兼任着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面要求我们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首先是要轮流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 我开开门,是老黑豆。他笑笑地说,“饭便当了,叫您过去。”我说,“今天怎么还是你们家?”他说,“夜儿是队上招待您。让我老婆给做。今儿才是在我家吃派饭。” 他头天就跟我“您您”的,我以为是沾了书记的光,没想到今天他还是这样的称呼我。 我说,“论年纪你比我父亲也大,以后叫我小曹就行了。”他说,“看您说的。您啥人我啥人。”听了这话,我不由地笑了一声。我说,“那你先回吧。我马上就去。” 我洗涮完出了门,他还在外边等着。说怕我认不得他家。路上,他说腿迟脚慢的,让我头走。看他那客气得有点委琐的样子,我没再跟他说什么,头前走了。他不远不近地跟在我屁股后头,倒好像是他不认识家,由我给领着路。 一推他们的堂屋门,见杨司机圪蹴在地下给仙云的那两个光头小弟弟洗脸。俩家伙不好好儿洗。有一个像挨了刀的猪尖声地怪叫,有一个像猪吃食似的弄得满地都是水。杨司机在他们的后脑勺一人给了一巴掌,他们才安静下来。我心想说,他怎么又在这里,还给孩子们洗脸,还敢伸手打他们。我很纳闷儿。他是他们家的什么人? 从老黑豆家返回排房,伙房的门开着,别的知青都还没过来,只有小高一个人在做饭,我就问她。小高说曹队长您刚来不知道,这村的稀罕事失笑事儿可多呢。她笑着说,他们那是共家呢。 “共家?”我说。 “也就是朋锅。”她说。 “朋锅?” “也就是伙伙儿过着呢。” “伙伙儿过着?” “就是那个,那个,您慢慢就知道了。” 见小高绕弯着不往明说,我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实际上当时她已经说明白了,只不过是我从没听过“共家”、“朋锅”这类的词儿,所以就理解不了“伙伙儿过”的意思。 “您哇看不出?仙云的那两个弟弟是砖头的。”她说。 “杨司机?”我说。 “上边的三个女的才是老黑豆的。” “这五个孩子的妈,是一个妈?” “是一个。” “这么说,她有两个男人?” “他们这是明着的。村里还有几家暗的。” “暗的?” “不公开,但人人都知道。” “他们也都知道人人都知道?” “噢。” 小高说完“噢”,红着脸笑了。我也觉得太有点刨根问底了,就把这话题打住,问开了知青的伙食。 半夜,又是在睡得正香的时候,我又听到了有人在奔跑,就跑就“杀人——杀人——”地喊叫。这次我没急着往起爬,我只把头仰起来侧着耳朵听,同时脑子里判断着是不是在做梦。我能听出那人是由远处向排房跑过来又跑了过去。我还听出那人不是大步跑,而是迈着碎步在急急地跑。我还听出只有他一个人在跑。他没在追什么人,也没有人在追他。我扒在窗帘缝儿往外瞅望,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那声音过去了,再后来就听不着了。我拨着手电看看,半夜三点。和上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间差不多。 那次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梦,白天也就没跟人说过这事,也没有问问别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第二日我跟小高打问,村里是不是有个疯子。她说没有。我说我黑夜听到有人喊杀人。小高笑着说那是老黑豆又犯了夜游症,他心一不顺就犯这种病,一年总得犯个几回。半夜出来喊一圈儿又回去睡觉,白天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真有意思。这个喊叫着要杀人的人竟然是老黑豆,是那个连筷子都拿不动的小老汉。 社员们都是集体劳动。 每当吃完早饭和中午歇完晌,刘书记就站在当村的井台上,两手圈住嘴,喊: “社员们啊——动弹哇——出来受哇——” “老年队耕地——” “青年队修路——” “妇女队和男人队打场——” “社员们啊——动弹哇——出来受哇——” 他要喊这么四回。脚站在原地不动,光上身转,冲着东南西北各来一遍。 阳婆是书记的表,书记是社员的钟。 …… -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ISBN:9787540457372,作者:曹乃谦 著 -
佛的孤独
《佛的孤独:曹乃谦中篇小说选》内容简介——难以割舍的眷眷亲情,青涩淡淡的初恋情窦,纯真朴实的儿时友谊,激荡年代的插队记忆:那穗儿、那柳姐、那善缘和尚……他们的故事读来曲折哀婉、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常常令人震撼。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串联出一个纯真少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别样青春成长历程,透过少年的眼睛,折射出作者对生活深厚的感悟,对社会责任和良心的理性思考。 -
最后的村庄
《最后的村庄:曹乃谦短篇小说选》是其数年呕心沥血之作,精选了其短篇小说作品。全书共收集了21篇短篇,分别是:野酸枣、沙蓬球、最后的村庄、斋斋苗儿、亲圪蛋、黄花灯、英雄之死、小寡妇、老汉、忏悔难言、小精灵、不可难闻、山药蛋、山丹丹、豆豆、根根、荞麦、苦杏仁儿、孤独的记忆、老汪东北蒙难记、豺狼的日子。篇篇描写山西农村生活,作者原封不动的使用生活口语、山西方言土语和极具山西特色的民歌,语言独特、真实而准确。 -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他的文字,但由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说过,“曹乃谦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开始关注他。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由29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汇成一个长篇小说,小说的背景是1973年、1974年的塞北农村温家窑,故事里头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可怜的光棍儿,除了渴望吃饱以外,他们都渴望跟女人“做那个啥”。书中对食欲和性欲饥渴的描写达到了极至,而曹乃谦这个37岁才开始写小说、现年58岁的大同警察说,书里写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书中多次出现的“要饭调”使全书有一股浓浓的莜面味。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温家窑是曹乃谦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1974年曹乃谦曾被派到这里给插队青年带队,在温家窑一年的生活,深深震撼了曹乃谦。而那首在当地叫“要饭调”、“烂席片”的信天游,也成为了他小说的“主旋律”。 当年因为和朋友打赌,曹乃谦开始写小说。1988年《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得到了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好评。汪曾祺还向曹乃谦建议,书名可以改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而这个题目则取自书中唱到的“要饭调”:“白天想你墙头上爬,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不过,当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完成后,却在国内经历了10年无出版社问津的尴尬。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曹乃谦遇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在他的推荐下该书才由台湾地区天下文化书坊出版,后来又被马悦然翻译成瑞典文出版。而在沉寂多年后,这本被誉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今年4月底终于在内地面市。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