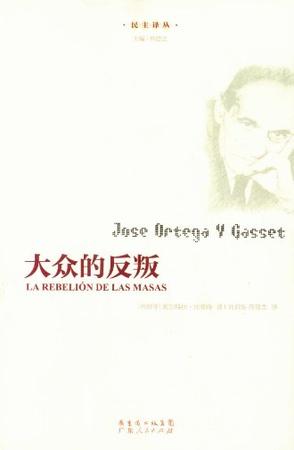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奥尔特加·加塞特
-
生活与命运
书摘:真理所面临的奇妙探险 在艺术、爱情或思想方面,我想任何事先的计划和宣示都是没有用的。以思想来说吧,对任何问题的沉思默想,如果是真正在想,就必然会使有思想的人摆脱流行的见解,摆脱那些可称为“一般的”或“普遍的”的见解。因此,所有理智上的努力,都可使我们脱离陈腐的言论,透过隐密而困难的途径,然后把我们带到一种前所未见的境界,于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异乎寻常的思想之中。这就是我们沉思默想的结果。 现在我们知道,事先的宣示或计划,是要去预期这些结果,把前面的道路弄平,并显示这些结果将被发现的终点。但是,以后我们会知道,如果我们把思想与获得思想的心路历程分开,而使思想像孤岛一样的独立而突兀的话,那么,这个思想便是最坏的抽象思想,也是无法令人了解的思想。当一个人一开始研究就告诉大家最后他所希望找寻的东西时,那么他要获得的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最后会产生哲学的探索呢? 所以,我不想把这些演讲的主旨,作成蓝图计划。当此开始之际,只想先表明我以往的出发点,亦即你们现在的出发点。 我们从一个显著的事实开始,这个事实即是今天所产生的哲学思想与本世纪初期的另一种与此非常不同的哲学思想,二者所持的共同观点,以及哲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像所有共同的和外在的事实一样,前者可以用外在的方法加以证明;例如,我们可以在统计数字上比较一下今天的大众和30年前的大众在哲学著作方面的购买量。今天,大家都知道,几乎每个国家,哲学著作的销售量都多过文学作品的销售量,同时,无论你向哪方面看,都可以发现对观念科学的好奇心正在不断增加中。这种好奇心由两种成分构成:一方面,大众开始感受到自己对思想的需要,同时,也在思想中感到某种感官上的快乐。这两个特性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所有发自内心而非偶然外来的基本需要,都会带来某种感官上的快乐。感官的快乐乃表面的快乐。当每个人完成自己的命运,即实现自己,成就自己的本来面目时,便会感到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施莱格尔便将快乐与命运之间的关系颠倒,他说:“我们对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具有天才。”天才是人类完成某种工作的最高才能,经常带有最大的快乐。稍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个人的命运会成为他最大的快乐。 与过去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显然具有哲学的运命;所以,我们在从事哲学思索活动中得到快乐——当我们竖起耳朵听公开的哲学讨论时,或是成群结队地跑到哲学家身边正如跑到游客身边去听从别处带来的消息时,我们便得到快乐。 这种情形与一百年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同时我们从今天普遍在某方面相同的改变中发现,今天的哲学家,是以一种与上世纪哲学家完全相反的心情来面对哲学的。所以,我们打算先谈谈为什么我们以一种与过去哲学家不同的心境来接近哲学的理由。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一直向前进行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现在很难把它表示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了解它。我们继续以迂回的方式向它推进,愈接近它,迂回的圈子愈小,同时,每当我们环绕一次,便产生更大的紧张,从冷漠、抽象的外部,进入非常亲切的内部。所以,哲学上的大问题需要一种像希伯莱人夺取杰里科及其中的玫瑰花园时所用的战术一样:不作直接的攻击,只慢慢地包围着,一步步缩紧包围圈,同时,空中又保持着让人紧张的号角声。 我希望这种紧张不会松弛,因为我们现在所开始的道路,在本质上是会愈往前走愈有吸引力。我们从刚才所说的外在问题,进行到更为直接的问题,进到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有关的直接问题上。我们准备大胆地进入人们通常所谓生活而其实只是生活外表的更下一层;穿过生活的外表,我们要进入自己生活的基层,这一层替我们保持着最内在的存在奥秘,最深刻的自我奥秘。 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我这样说,并不是作事先的宣示;相反地,由于从扰嚷城市中来的听众意外地多,这是我不得不采取的一种防卫或预防。在《什么是哲学?》这个题目之下,我发表过一次学术性的讲演——因此,也是严格科学的讲演。我不知对这个题目的误解是否使很多人认为我在对哲学作基本的介绍;易言之,即以表面而简单的方式讨论传统哲学中的复杂问题。我必须澄清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只会分散和扰乱你们的注意力。我想做的正好与此相反:我希望探讨哲学活动本身,哲学思索本身,并对哲学活动、哲学思索加以根本的分析。就我所知,这种工作从来没有人做过,当然,更没有人以我现在所具有的决心来从事这个工作。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似乎属于最具学术性和专门性的问题,只适于哲学家探讨的问题,根本不适合一般人讨论。如果我们讨论它时偶然碰到那些与人类较有关系的题目,如果我们严密探索哲学到底是什么时,突然落到与人类最有关系的题目上,突然落入亲切而活跃的生活核心,并发现自己在探索那些日常问题,甚至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问题的话,这也许是因为它必须以那种方式存在,因为我的专门学术性问题的学术性发展需要它,而不是我自己在吹嘘这些问题,寻找这些问题或事先想到这些问题。我所宣示的唯一东西,与这完全相反。所以,我仍然不受任何约束,可以随我自己的意思而不否定这种说法所带来的任何理智上的困难。 同时,我必须尽我最大的努力,使你们都能了解我所说的话,甚至使那些过去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也能了解我所说的话。我总认为“明晰”是哲学家对读者们应有的礼貌,而且,在我们向所有人类宣讲并使他们能够贯通其探索以前,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训练使我们觉得这在今天比以往更是一件攸关荣誉的事。这与各种特殊科学不同,因为特殊科学不断在其发现的宝藏与凡俗的好奇心之间,加上它们特有的专门术语。我想,当哲学家在研究和探索真理时,为自己的目的着想,就要有严谨的方法,可是,当他准备宣布他的真理时,便应该避免某些科学家向大家卖弄技巧以自娱的那种讥讽手腕。 所以,我说我们觉得今天的哲学与上个世纪人们对哲学的看法,是不太相同的。但是,我们这种说法,是表示我们承认真理在改变,以往的真理成了今天的错误,而今天的真理,明天又将没有用处。这种说法是否剥夺了真理的尊严呢?怀疑主义中最有名的论证是阿格里帕所谓语言的象喻,认为各种教条之间缺乏连贯性。对真理所持的观点的不同和改变,对各种学说理论所具的信心的不同和冲突,使我们产生了怀疑。所以,让我们现在继续去面对这个怀疑主义。也许你们不止一次想到过真理所面临的奇妙探险。例如万有引力定律:从它有效的范围内看,无疑这个定律是有效的,自有物体存在以来,物体的活动就永远遵循着这个定律。然而,这个定律要到17世纪某一天才被不列颠群岛中某一岛上的某一人发现。说不定有一天人们会忘记这个定律,并非因为我们排斥它的完全真实性而反对或修改它,只是纯粹地忘记它,同时,更回到牛顿发现它之前人们所处的那种对它不起怀疑的状态。这种脆弱性使真理具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双重地位。从各种真理本身来看,它们永远存在,毫无改变或修正。然而,它们的被发现,它们的落入时间范畴中,则使它们具有历史性,它们在某个时代广被奉信,也许在另一个时代却又消失不见。显然,这种时间性并没有影响它们,但却影响到它们是否为人所知。真正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用以思考它们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这是时间中真正发生过的变迁。具有历史过程的,是我们认识或不认识这些真理的事实。使人觉得神秘而不安的就是这个事实,因为,透过我们的某一思想,即透过一个最短暂世界中一种瞬息即逝的实在,我们把握到某种永久性和超时间性的东西。那么,思想是两个内容不同的世界合在一起的地方。我们的思想不断地产生、消逝、传递、服从其他思想的支配。同时,它们的内容被思想的东西,却仍然不变。二加二等于四,当我们用来了解这个真理的理智活动不发生作用时,二加二仍然等于四。可是,即使这样说,即使说真理永远是真理,也是不恰当的。所谓永远存在是指某种东西在所有时间中的持久存在,是指无限的绵延;所谓持久还是指长存于时间的急流中。 那么,好了,真理并不持续长久时间或短暂时间,真理根本没有时间性,根本不落入时间的急流中。以我不正确的判断来看(我们以后会了解是因为哪些基本理由),莱布尼茨曾称之为永恒真理。如果永久的东西(thesempitirnal)和整个时间一样的持久,那么,永恒的东西(the eternal)将存在于时间开始之前,终于时间结束之后,但它本身却包含一切时间,它是超绵延的绵延。这种情形使它一方面消灭绵延,同时又保留绵延:一个永恒的东西,历经无限的时间,换言之,它持续片刻,也就是说,它并不持续,它以一种同时的和完全的方式,拥有一个没有终结的生命。事实上,这就是波伊提乌对永恒性所下的精妙定义。但真理对时间的关系并不是积极正面的,而是消极反面的,它只是在任何意义下都和时间不相关,它完全脱离一切时间的限制,完全在时间之外。因此,严格地说,如果我们说真理永远是真的,这和我们说——用莱布尼茨所用的有名例子——“绿色的正义”,比起来并不含有更多的恰当性。“正义”两字所含的观念实质,没有任何表示可以容许“绿色”这种性质附着其上,不管我们如何尝试把这种性质放进去,都无法附着到正义两字的意义上去,就像附着不到滑面上一样。我们无法把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纵使我们同时说到它们,也是彼此相离的,彼此根本无法联系在一起。真理的特色是非时间性的,这表示真理是一种非时间性的东西,这个东西与发现真理、思考真理以及认识或不认识、记住或忘记真理的人类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没有侄何差异比这个差异更大。可是,如果我们还说“真理永远是真的”这句话,从实际的立场说,那是因为它并没有带来任何错误的结果。诚然,它是一种错误,但这种错误却是无害的。由于这种错误,我们可以借自己在习惯上看世上万能的同一时间意识的方式,来看那真理所具有的奇妙存在方式。总之,说某种东西永远是某种东西,就等于说它独立于时间变化之外,不受时间的影响,在时问范围之内,这是最接近非时间性东西的特色,这是非时间性东西的类似形态。 因此,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将真理即其所谓的“理念”(Ideas)置于时间性(即现实世界)之外,所以他创造了另一个超现实的类似世晃,即天上的世界。虽然这在柏拉图思想中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我们承认,就作为象征的比喻而言,它是很有用的。它使我们看到在时间性世界(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根本的世界,非时间性的真理就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但是我们要注意,有时候,这些真理之一,例如万有引力定律,从超现实世界中渗入到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好像透过一个扩宽的裂口一样。观念像流星那样被投入人类和历史世界中——这是一种“降临”的象征,是在所有承认上帝存在的宗教心灵深处悸动的降临观念。 但是,这种降临观念,这种另一世界真理渗入我们所处世界的观念,带来一个非常严重而充满暗示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仍值得加以研究。这个可以让真理越过的裂口,不是别的,就是人类的心灵。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种真理也像其他类似的真理那样,已经事先存在而与时间无关,那么,我们为什么明了这种真理,为什么在某天某人会抓住这种真理呢?为什么以前没有想到它或以后没有想到它呢?为什么它的发现者不是别人呢?显然,这是与那真理的轮廓和真理所通过的裂口的形式,即人类主体之间的问题密切相关。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说万有引力定律到牛顿时才被发现,显然牛顿和这定律之间一定有某种密切的关系存在。这种密切关系是什么呢?是类似关系吗?现在,我不是想把问题简化,相反地,我是想强调这个问题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一个人怎能与某种真理——例如几何学上的真理或任何其他真理——以任何方式相类似呢?毕达哥拉斯这个人有什么地方与毕达哥拉斯定理相似呢?学生们也许会开玩笑说毕氏定理可能与他的裤子相似。问题是毕达哥拉斯并不穿裤子;在他那个时代,只有塞西亚(Scythians)人才穿裤子,可是塞西亚人并没有发现这个定理。 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使我们的哲学与过去几百年风行的哲学的基本区别。这个区别是考虑到某种非常根本的东西:即思考、了解或想象某种东西的人与他所了解或想象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类似;相反地,其间却有着一般的差别。当我想到喜马拉雅山时,从事思维的我以及我的思维活动都与喜马拉雅山山峰不相似:山峰是一片占有广大空间的山,而我的思维活动却毫无山的痕迹,甚至也不占些微的空间。如果我不是想到喜马拉雅山而是想到“18”这个数字,情形也是一样。在我的意识、生命、精神、主观的自我中,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成为“18”的东西。像显著的特征一样,我们可以说,我借以思考18个单位的这个思想活动,其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你们说这其间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两者显然是不同的东西。 -
大众的反叛
《大众的反叛》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是“大众民主”正在成为欧洲政治生活主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强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 这一切,都被奥尔特加敏锐地察觉到了。在《大众的反叛》中,作者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深深的恐惧,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 《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作出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之内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有巨大帮助。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